此片有360度无死角的经典范儿,但仍功败垂成_加里奥德曼_希区柯克_优秀演员
如果有哪位导演能成为本世纪的「优质电影传统」典型,乔·赖特或许能榜上有名。

乔·赖特
当然,这里说的是特吕弗在1954年口诛笔伐的那种「优质」导演——专门挑选经典文学或者历史题材来进行改编,其庞大的成本与精良的制作却难掩其平庸的姿态;相反,特吕弗从希区柯克曾被认为是低级娱乐的悬念片身上,发现了那些平庸人士做不到的东西。如今希区柯克的电影早已成为了至尊经典,上了大雅之堂,与此同时,曾拍摄《安娜·卡列尼娜》和《赎罪》的「优质」导演接到了新的任务——改编一部「希区柯克式」的悬疑小说。然而在《窗里的女人》(和弗里茨·朗1944年的影片同名)开场不到几分钟内,就在《后窗》结尾高潮的片段直接开始在女主角的电视机上播放的时候,这部所谓的致敬之作就已经给自己宣判了死刑,这部教科书级的糟糕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反例。

《窗里的女人》
影片直接的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艾米·亚当斯。她饰演的儿童心理学家安娜患有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成天呆在自己巨大的公寓里以看老电影和酗酒等方式消磨时光。她还像《后窗》里摔断腿的詹姆斯·斯图尔特一样,喜欢偷窥街对面的邻居,直到有一天,她见证了一场谋杀……

《窗里的女人》

《后窗》
亚当斯显然是一名技巧出众的演员,她能轻易地成为导演想要的那个精神疾病患者的形象,但影片中她的存在却难以给人任何印象。我们不会看到在《大师》中,她扮演的邪教教主妻子面对华金·菲尼克斯,在特写中眼睛由幽静的深蓝化为黑色的超验时刻;我们也不会听到《降临》中,她饰演的语言学家说起未来将发生的故事时那宁静却深邃的独白。

《降临》
这些时刻中暧昧的动机让我们意识到人物内部不可言说的秘密,但在《窗里的女人》中,艾米·亚当斯只是一个工具,也没有真正的语气可言,于是只能以方法派的陈腐方式试图「挖掘」一个角色的内心。但这一切都是自说自话,连心理治疗都称不上。亚当斯并非唯一一个被影片摧毁的优秀演员,同样的结局还发生在了饰演街对面的邻居的朱丽安·摩尔、加里·奥德曼、詹妮弗·杰森·李等演技派明星身上。

《窗里的女人》
当然,影片只把这群人当作「明星」。如何指望一部电影能让这样的人保持在窗户的另一边?几乎可以想象制片人说:我们付给某某某几百万的片酬,不是用来让他们站在街对面的!在《后窗》中,邻居们被主角观看,希区柯克将视点严格控制在斯图尔特的公寓内,绝不会跨过窗户去拍摄,甚至当她是格蕾丝·凯莉时也是如此。也正是因此,在影片的最后,「另一边」闯入到公寓时的气氛会如此充满恐惧——因为我们作为电影观众的「安全空间」(电影院/斯图尔特的公寓)突然间遭到了来自「电影」内部形象的威胁。

《窗里的女人》
相反,乔·赖特和他的编剧小组没有一分一毫的耐心,一定要让所有的邻居(「明星」)一个个登门拜访后才能勉强让观众知道他们是谁,而希区柯克从几十米外便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孤独的钢琴家、自导自演着浪漫悲剧的中年妇女、让斯图尔特「胆战心惊」的新婚夫妇、还有美艳的芭蕾舞演员等。这些被封印在各自窗里的角色都拥有自主性,同时也在斯图尔特的观看下,隐隐连接着他的意识,希区柯克在说的,正是电影和观众的连结。回到本片。当然,为了完成「致敬」任务,还是得设计些「情节」,让亚当斯到窗边举个相机东拍西拍,但节奏是如此逼人(丹尼·艾夫曼的配乐爆炒着沉闷的画面,没有任何用处),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窗里的女人》
电影并没有任何观看什么的兴趣,它只在乎那些最乏味的「心理活动」和反转,和一些符号化的迷影装饰:《迷魂记》式的漩涡和楼梯当然得登场,结尾「治愈」的主角离开公寓的全景则和《艳贼》的最后一镜如出一辙,但全片充斥的妄想症气氛让观众很难放心进入到这个情境中,生怕导演还有什么别的阴谋藏在别处。

《窗里的女人》
信息是它唯一在乎的东西,里面有一些相机取景器的第一人称镜头,但好奇心是不存在的,只有寻找「谁杀了谁」的线索,除此之外它只能四处摇动,放大缩小,无谓地飘荡着。变焦镜头拉到特写的景别,是终极的隐喻:没有影像,没有画框,只需要寻找信息。

《窗里的女人》
当然,并不是说导演一定要遵照《后窗》的每个镜头机位进行创作(格斯·凡·桑特一比一翻拍的98版《惊魂记》或许是前车之鉴),但这正是最大的讽刺:正确的机位只可能有一个,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看《后窗》呢?而演员则遭到最大的折磨,她们试图寻找着什么正确的表情来「表现角色的内心」。
朱丽安·摩尔和亚当斯对着干瘪的台词,互相冷笑着;加里·奥德曼演的父权角色怒吼着什么东西,但完全不存在詹姆斯·曼森在尼古拉斯·雷的《高于生活》中绝对的恐怖,我猜丘吉尔先生和乔·赖特可能还沉浸在《至暗时刻》冲帝成功的幻觉中呢。当然,影片还需要时不时穿插某种「心理治疗」场景来帮助观众了解人物,这点即便是希区柯克也不例外。

《窗里的女人》
但《窗里的女人》只能将自己视为「严肃的精神创伤人物肖像」,而《后窗》中,瑟尔玛·瑞特饰演的护士对斯图尔特的幽默讽刺却彻底消解了悬念片的妄想症候,反而给电影基调铺上了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式的动感和语气。

《窗里的女人》
艾米·亚当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的身份是这部以羞辱为乐的电影最后的阴谋:是啊,她因为服药后神志混乱,看到了幻象,甚至可能是一场谋杀,我们该相信她的话吗?影片的一众角色借此对主角展开攻击,觉得这个可怜的疯女人玩着「狼来了」的游戏。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精神分裂似的两面夹击:一方面,导演和演员尽力用各种花哨技法展现患者的所谓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各种外部力量不断否认着她,拒绝承认她的意志。但电影应该相信自己的人物,即便如《穆赫兰道》一样,一切都是梦境,但林奇知道只有拍摄所有虚幻的,理想中的美好,才能让观众爱上人物,并最终真正了解到她内心的痛苦,这也正是希区柯克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学到的:林奇、埃里克·侯麦、或者布莱恩·德·帕尔玛都深谙这点——像《迷魂记》中的斯图尔特一样,真正爱上一个形象,即便最终跌入骗局,或者像《惊魂记》那样,实施着共情力的魔法。

《迷魂记》
不应该羞辱角色,因为电影是用来观看的,而不是自导自演的阴谋。艾米·亚当斯在片中看的另一部电影是奥托·普雷明格的《劳拉秘史》,这部黑色电影经典讲的正是关于信任的微妙流动,对日后的重要作品如《双峰》影响深远。影片中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不可靠叙述者」,但他们为了保护一些东西,不得不相信自己的谎言和盲区,而电影总是冒着被骗的风险在拍摄——演员没有任何心理化的描绘,而仅仅是陈述着他们所抓住的真实。

《窗里的女人》
饰演专栏作家的克利夫顿·韦伯的画外音贯穿电影始终,是影片情感脉络的引导者,而最终我们也正是因此面对着一个矛盾,即便案件揭晓,谎言被戳穿,但回想之后便会发现,这一切都不妨碍他说的事实——属于情感的事实。好奇的是,《窗里的女人》引用了这么多经典名作的表面,但它真的从中学到了什么吗?这部影片本应该是福斯影业最后的冲奥扛鼎之作,但现在它仅会存在于网飞的万千片库中,即将被遗忘。
关注电影帝国公众号,订阅更多奇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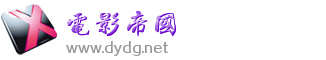 电影帝国
电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