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界,崇高之物与齐泽克电影理论:第二章 电影中的崇高客体(下)_希区柯克_多萝西_齐泽克
象征界、崇高之物与齐泽克电影理论
原名:The Symbolic, The Sublime, and Slavoj iek’s Theory of Film
原作者:Matthew Flisfeder
翻译:加速器
校对:snoper卓尔
编辑:snoper卓尔
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Capitalism法权,请联系并提醒原po卷铺盖删文跑路。
本文目录:
1 作为寓言的电影:希区柯克的案例
2 希区柯克:变态狂
3 为什么《惊魂记》全然是关于倒错的电影
4 回到《惊魂记》里的精神病
5 凝视如何作用于希区柯克电影
6 林奇宇宙;或,实在界的侵入
7 女人“并非整体”
8 两种蛇蝎美人
9 作为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





在电影《伸冤记》的开头,希区柯特亲自现身向观众做开幕演说,却因此夺走了我们对电影的幻想纬度。开头的信息适得其反,他告诉我们电影基于现实事件改编,试图使电影中的现实比看起来更加真实,但这反而剥夺了观众用以感知象征界“现实”的幻象之维。齐泽克认为,幻象构建了“现实”。希区柯克宇宙中的幻象之维正是被包含在了其揭示的寓言模式(allegorical mode)之中。
齐泽克对于希区柯克宇宙之寓言维度的观点有赖于他个人对现代主义寓言的精确定义。在传统寓言中,叙事内容只是作为某种先验原则的表征而运作:例如爱,荣誉,背叛等等。与此相反,现代寓言则在讲述自身;它是自我指涉的,被言说的内容(叙事的空间)关涉自己的言说过程:被言说之物的形式不仅仅包含形式技巧或是被言说之物的内容特征,还包括整个言说的生产过程[27]。在希区柯特的大多数电影中,后者需要借助自己在(希区柯特电影中)被言说内容中的特定位置,才能确定自己与观众的关系。而在《伸冤记》中,寓意之维被直接揭示出来。因此,希区柯克的寓言被从其宇宙中抹除——它过于直接地指出了自己的言说过程,所以失去了位于希区柯克宇宙核心的幻想之维。换句话说,希区柯克在《伸冤记》中说的太多了。
齐泽克对《伸冤记》的解读被当成一种区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批判模式的方法。他声称经典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将希区柯克对电影的开场介绍,视为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符号。他们会声称,这部电影悬置了寓言之维,因此才能非常接近(过于接近)直接的社会批判。从他们的角度看,寓言之维应当是不可视的并且无涉于社会批评的。但齐泽克却坚持认为,反而是因为希区柯克电影严格遵守寓言之维,才会给电影刻下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印记[28]。正是这种态度使齐泽克后来声称,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从纪录片向剧情电影的转变,能更加有效地接近实在界。纪录片太真实了,因此无法引导观看者抵达任何地方。相比《伸冤记》中直接的“社会批判”,齐泽克还提出了一种对《惊魂记》的拉康式解读,准确地展示了希区柯克宇宙的寓言维度如何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
齐泽克称,《惊魂记》是展示希区柯克像“仁慈的施虐狂”一样玩弄观众的幻想最为明确的例子——如同残酷的杨森主义上帝。 在这一点上,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对齐泽克的(含蓄的)批评似乎是正确的。在讨论了希区柯克宇宙之寓言维度的重要性后,齐泽克转而开始解释拉康的萨德幻想图式。
最开始,萨德幻想(VS)的图式讲述了萨德式的主体努力用他人的痛苦来满足自己的享受。

萨德式主体对他者施加痛苦,以此确证自己的存在。然而,拉康在《康德同萨德》中却声称,在“施虐狂”与受害者的表面关系下,还存在另一种潜在的关系。后者道出了前者的真相并出现在图式的下半部分:即(a $)——对象小a和“划杠的”分裂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施虐者施加的痛苦,实际上是一种供他者享乐的“客体-工具”。从这方面来说,施虐狂施虐并不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是为了他者的享乐[29]。然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一个图式解释了何为萨德式幻想。此外拉康还介绍了另一个图式,解释了萨德式幻想在另一个决定性框架中的位置。

把第一个图式简单旋转,就可以得到第二个图式。它显示真正在渴望施虐幻想的主体正是“客体-受害者”(a)。因此施虐狂被表现为受害者。齐泽克在这里提及拉康的施虐狂倒错图式,是为了指出,萨德式的僭越行为虽然乍一看是企图颠覆律令,但其最终效果却是在制定律令。就像齐泽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倒错不是颠覆——那么为什么需要剖析萨德幻想图示呢?
在希区柯克电影中,终极的施虐者变态狂只能是希区柯特本人,他向观众灌输着“享乐意志”——强迫观众承认,他们是遵循自身的意愿,来体验屏幕上属于他们自己的倒错的暴力行为——随后再给予观众其所欲望之物,以向观众表明,他们实际上是被真正的施虐狂希区柯克所操纵的。施虐性的希区柯克式寓言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运作因此向观众显示,在他们可以认同象征界框架中的电影“现实”之前,他或她必须首先将自己认同为“纯粹的”凝视——即客体的凝视:对象小a的凝视。
齐泽克认为,希区柯克式寓言的基本策略是,以某种自反性的方式将观众的凝视纳入电影本身,形成了对观众欲望的病理性本质的不完全意识(partial awareness)。齐泽克声称,从作为象征性认同的点的凝视(即大他者的凝视)到作为客体的凝视(小他者,对象小a的凝视)的转变,迫使观众认同自己的欲望(虽然这种欲望尚未浮现在意识层面)。这是一种被铭刻于在电影景观里看似中立的凝视上的欲望。他这里提及了《惊魂记》中诺曼·贝茨目睹玛丽安的车陷入他母亲的房子后面的沼泽中时的场景。此刻当车停止下沉的那一刻,观众的焦虑感被激起了。齐泽克说,那一刻,观众将自己的欲望认同为诺曼的欲望。他的观点是,在这个场景中,看似中立的电影凝视被主体化为观众自身欲望的不完全凝视(Partial gaze):“观众从电影一开始就被迫假定他或她目击的场景正是为了自己的眼睛而上演的。[30]” 在《电话谋杀案》中,当凶手对妻子的谋杀未按计划进行时,我们也能对反派怀有同样的认同。当事情并非如愿时,观众的期望会被颠覆,但正是这种颠覆表明了出自观众的一种想要谋杀妻子的施虐性“享乐意志”。
这种欲望被体验为僭越(transgressive)。观众所体验的欲望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社会允许的规范。如此可见,正如齐泽克所说,倒错以这种方式,成为了一种社会建设性(而不是颠覆性)力量。然而,正是观众对这种僭越态度的认同,标志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当希区柯克最墨守成规地出现并称赞诸如法治什么什么的时侯,意识形态批判已经完成了:正是这种对“僭越”式享乐的根本认同,凝聚起了一个社群[31]。对律法“内在的”僭越,是真正将符号性社群凝结在一起的东西—— 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在认同律法的文字,而是认同一种特殊形式的享乐,一种僭越性的享乐——这一社群规范着我们与象征界的日常联系。正如齐泽克经常指出的那样,当一个人学会如何适当地违反规则而非遵守规则时,他才能真正成为社群的一分子。当我们都认同同一种被文化允许的僭越时,社群才得以形成。这种运作方式在《惊魂记》被给予很高的权重,因为观众被迫不断重新组织起自己的认同点。
影片的主观视角不断变化,从玛丽安开始,然后是诺曼,然后是亚伯盖兹,最后是山姆和莱拉。这种持续的转变迫使观众不断置换认同位置。而齐泽克则认为,观众对最后三人视角的认同是次要的,是从属于对最开始两人即马里恩和诺曼的认同的。在玛丽安被谋杀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去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人物了。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这是因为叙述呈现的角度摇摆于当代日常生活的表面和淫秽黑暗的背面之间——简单地说,它在象征的“现实”和淫秽的幻想之间摇摆。这是从歇斯底里的欲望到精神病驱力的通道:对象小a的两个侧面。
欲望和驱力之间的摇摆道出了被幻想区分开来的对象a的正反两面。在欲望图式中,对象小a是欲望的“客体-成因”。它是被“客体化”的匮乏。因此,对象小a并不是主体所欲望的客体。它实际上是客体化的大他者(与小他者相对应的大他者(grand Autre),对象小a)之匮乏,并使欲望不断流动。这种不懈追寻能满足欲望的对象的行为(欲望自反性),产生一种剩余享乐。与此相反,驱力则是失败的享乐。驱力,或是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在无法充分享乐与满足欲望的失败中产生快感。这种享乐,能够回到最初匮乏的位置,从头再玩一次“游戏”。根据齐泽克的说法,《惊魂记》在歇斯底里的欲望和精神病驱力的两个界域之间游动。
歇斯底里和精神病之间的区别可以被认识为,主体与象征秩序的关系,及其对“父法”或“父之名”的服从与否。“歇斯底里所处的位置,是服从于父亲隐喻的权威的:也就是禁止欲望满足的律令。歇斯底里主体所处的位置禁止享乐,但同样也是这一位置使得在欲望中获得剩余享受成为可能。因此,歇斯底里主体位置屈服于父之名的象征权威。但是,精神病则会坚持母性他者((M)Other)的欲望。在歇斯底里主体所处的位置上,律法的禁令使欲望得以可能;但精神病却并不承认这一可能性条件,并执着于客体化的、位于象征界外的不可能的欲望客体。齐泽克认为,诺曼·贝茨仍然是精神病驱力下的囚徒,因为他没能认识到接触欲望是不可能的,不在场的父亲的隐喻没收了他的欲望。正如他所说,诺曼是一种先于语言(vant la lettre)的“反俄狄浦斯”[32]。然而,《惊魂记》在欲望和驱力之间的运动并不只局限于主角的心理经济。这一运动在电影中两个最有冲击性的谋杀场景中,还产生了电影式的效果。
淋浴场景突如其来。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前半段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暗示。齐泽克说这一场景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分散了观众对第二起谋杀案的注意力——即侦探亚伯.盖兹被谋杀一案。淋浴谋杀场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纯粹是通过电影“设备(devices)”来完成的:精细的剪辑、特写镜头等等。我们没有见到玛丽安被谋杀的实际场景,这里是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刀直接刺穿她的身体。齐泽克认为,第一个谋杀场景对观众的影响,使第二起谋杀案似乎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第一起谋杀,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驱力的主体化;而第二起被预期的谋杀则是在玩弄欲望。因此影片的创伤性效果在于,观众在享受第二个谋杀场景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特定的(剩余的)享乐:作为观众,我们渴望(desire)亚伯.盖兹的死亡!
然后,回到希区柯克式的寓言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他的电影中,“凝视”是如何运作的。与银幕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凝视”理论相反,依据拉康研讨班XI《精神分析的四个概念》(1963-1964)中的理论,“凝视”来自客体而不是主体。正如琼·科杰克(Joan Copjec)所说的那样,银幕理论家经常混淆拉康的凝视概念,将拉康的“镜像阶段”和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凝视概念混为一谈[33]。基于杰里米.边沁的全景监狱理论,福柯认为主体是通过想象监视凝视海量在场来自我规训的。电影理论家们已经接受了凝视的概念,认为是观众占据了电影中凝视的位置。而拉康的凝视则是一种客体的凝视:它是“视界驱力(scopic drive)”领域中的对象a[34]。这诡异的凝视,在拉康意义上,真真切切遍布整个《惊魂记》。
首先,它看起来是一种“石化的凝视(petrified gaze)”。电影中恐怖的凝视,被一名特定的角色主体化,暗示了一个观众尚未意识到的可怕的污点。主体化的目光凝视着屏幕外、画面外的某些东西,最终落在观众自己身上。在齐泽克看来,这种回望观众的诡异凝视,是希区柯克杨森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提醒观众电影言说的过程。这些场景的对象a——比如诺曼在电影结尾的凝视;莱拉惊恐地凝视着母亲的房子——就是凝视本身,是看向观众的凝视。然而,这种凝视还打开了象征现实的“创口”。这里的凝视是象征性“主人能指”不曾中介(unmediated)的实在界的污点。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在“现实”的构成中,作为剩余而存在的两种运作元素:对象a(崇高客体)和空无的主人能指(没有所指的能指)。这两种元素缝合起了符号秩序的领域。主人能指如同线一般,“缝合了”象征现实领域——或者说是作为电影文本的象征效力(symbolic efficiency),缝上了实在的凝视打开的创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理解拉康语境下的希区柯克式寓言,是如何打开象征秩序的裂缝了。希区柯克宇宙揭示了现实的污点,是实在界对于象征界的入侵,揭示了围绕着言说之精确位置的象征性“现实”构造。随后,主人能指被添加到由实在的污点打开的领域,以便缝合(关闭)象征的领域,继续避免实在创伤的侵入。
如果在希区柯克宇宙中有一辆沿着客体行进的列车,它前行的时间非常之长,长到足以缝上由客体打开的通往实在界的创口;那么相比之下,林奇宇宙则是关于,“现实(从安全距离观察到的)与极其靠近实在界的位置二者之间的不和谐”[35]。为了证明这一点,齐泽克举出了电影《蓝丝绒》(1986)的片头一段:“简单介绍这个如田园诗般的美国小镇,以及男主人公的父亲在草坪上突发心脏病之后(当他倒下时,水管喷水的模样仿佛在撒尿,尿液在诡异地超现实般地喷射) 镜头栽向草坪,展示出那里热闹的生命:昆虫和甲虫四处爬行,它们嘎嘎作响吃着青草。[36]”
齐泽克指出,这种手法 “过于接近现实”会带来“失去现实”的效果。也就是说,太多的实在(Real)会扰乱象征的“现实(Reality)”空间。林奇宇宙因此通过对象征界不排除任何事物地认同,从而在象征的空间中引出实在。林奇的电影不仅会用视觉手法表现这种效果,还会借助声音的运用。
齐泽克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蓝丝绒》的开场镜头中。昆虫吃草的图像伴随着在现实中难以找到的“诡异的噪音”。在林奇的宇宙中,这些诡异的噪音是“由不属于符号现实的客体引起的[37]”。它们从外面突入,不是基于任何属于电影的符号材质。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象人》(1980)中的噩梦镜头组中。对齐泽克来说,这里的噪音穿越了内部和外部之间边界的客体。噪音是一个实在的客体,它侵入了象征性“现实”的空间:它是作为客体的声音。“凝视”代表的是视界驱力(scopic drive)中的对象小a ,“声音”则是乞灵驱力(invocatory drive)中的对象小a。
林奇另一个关于声音的例子是《双峰与火同行》结尾“矮人(dwarf)”的不可理解的演讲。 齐泽克说,字幕归化了这场演讲,借助大他者的媒介赋予其意义。而大他者的媒介——即呈现出可理解意义的符号秩序——通常被是隐藏起来的。而据齐泽克的说法,在电影的演讲里,它的运作被揭示出来。齐泽克的观点是,《双峰》结尾的场景逆转了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公式 :这里的声音并非作为文本中隐藏的,虚幻的因素运作;而是呈现为明显的,自我透明的,残酷的,不可穿透之物。这个声音的呈现方式,准确地说,就像 “一个扰乱我们生活平衡的异物。[38]”
【译者注:注意辨析:
pas-toute : not-all并非整体(并非某个女人的全部)
pas-toutes:not-whole并非全部(女人)
详见布鲁斯芬克:https://zhuanlan.zhihu.com/p/112155840】
因此,齐泽克笔下的林奇将他的作品呈现为一种思考女性原乐概念的关键所在。拉康的“性化公式”区分了“男性(masculinity)”和“女性(feminine)”享乐方式的不同。在《研讨班XX:再来一次》(1972-1973)中,拉康给出了以下公式:

这些公式不是在探讨男性/女性享乐的本质,而是在说享乐的建构是性差僵局的结果。
“男性”的一边(左边)代表了通过排除的方式对实在界进行符号性地隐藏。(菲勒斯)能指Φ的普遍性当某些东西被排除在外时才能成立:那被排除之物便是作为“一小片实在界”的对象a。相反,“女性”的一边肯定了一种例外的立场——一种“并非整体”的立场 ——其中不是所有的元素都服从于菲勒斯功能。换句话说,“男性”是排除了实在界后的象征效力的运作结果,而“女性”则将被排除的部分归还给象征界,结果随着实在界出现在象征领域,象征秩序本身的逐渐破裂。女性,在拉康意义上,剥夺了象征现实的根本性剩余——它的“原始大谎”。在林奇宇宙中,最能表达女性的“并非整体”的人物正是《蓝丝绒》中的汉·多萝西。
正如齐泽克所解释的那样,多萝西(伊莎贝拉·罗赛里尼饰)因弗兰克(丹尼斯·霍珀饰)绑架了她的丈夫和孩子而陷入抑郁。弗兰克折磨着她,对她进行性勒索作为让她的丈夫和孩子活着的代价。影片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发生在中间,当时杰弗里(凯尔麦克拉克伦饰)躲在壁橱里并目睹了多萝西和弗兰克之间的施虐受虐的性交场景。不过,齐泽克对此发问:这一幕是为谁上演的?
第一种可能是,它当然是为藏在壁橱里的杰弗里上演的。齐泽克认为,这个场景模仿了基本幻象的场景,这是一个人在自我幻想时表现出来的。按照齐泽克的说法,这个场景有两个特点证明了这种解读的合理性:一是多萝西将蓝色天鹅绒材料塞进弗兰克的嘴里,二是弗兰克在氧气面罩中深呼吸。尽管这一场景有令人不安的暴力感觉,但这两个要素,对齐泽克来说,代表了一个孩子在目睹父母性交时会想象出的视觉幻觉。或许这是孩子在偷听父母做爱时可能会听到的。也就是说,这个场景就是一种对基本幻象的解释。
第二种可能是,这一场景是为暴力的、患有精神病的绑架者弗兰克上演的。多萝西和弗兰克两人都进行了一场表演——对于多萝西来说表演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她知道杰弗里正在衣柜里看(因为是她让他藏在里面)。两人似乎都表演过度了。然而,弗兰克虽然对杰弗里正在观看这一场景的实际凝视毫无察觉,齐泽克依然声称,在弗兰克的脑海中,这个场景仍然有来自杰弗里的虚拟凝视——但既然弗兰克不知道杰弗里躲在柜子里,他的过度表演又有什么目的呢? 对齐泽克来说,这一切关键在于弗兰克不断地对多萝西大喊:“你不要看我!”齐泽克指出,为什么她绝对不能看他?因为那里“没什么(nothing)”可看的——也就是说,这个场景上演的是弗兰克拼命试图掩盖(displace)自己的创伤性阳痿。那么这么看来,多萝西和弗兰克是“假装发生了一场狂野的性行为,从而向孩子隐瞒父亲的性无能;弗兰克所做的一切叫喊和咒骂,对性交姿势的滑稽模仿,都是为了掩盖了性交并没有发生。[39]”
齐泽克提出的最后一种可能是,这个场景是为多萝西自己上演的。齐泽克认为,这一场景上演的是女性抑郁的原始层面的例子,而弗兰克的野蛮攻击是对女性气质这个原始层面的认同。然后,这一场景突出表现了一种“绝望的‘治疗’尝试,以阻止女姓滑入绝对抑郁的深渊[40]”。对齐泽克来说,最后一种解读揭示了林奇宇宙中一个基础的,原始的事实:男人将自己视为女性凝视的客体,女性的抑郁则试图重塑加在女性身上的“男性”的因果秩序。
齐泽克在与朱迪斯·巴特勒和欧内斯托·拉克劳的辩论《偶然性,霸权性,普遍性》中指出,黑色电影原本并不属于好莱坞电影。它原本是法国战后批判电影的一类,后来才被好莱坞吸收与发展。因此,黑色电影代表了法国对好莱坞电影的凝视。同样的道理,英美哲学传统——主要在美国——所讲的后结构主义,通常指从德里达到福柯的一系列法国欧陆理论家,而德里达和福柯本人实际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所以,当我们用后结构主义解读黑色电影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用一种不存在的理论去解释一种不存在的电影体裁。这不正好说明了蛇蝎美人在男性/男权话语中地位的重要性?蛇蝎美人是邪恶的一类,因为她既能支持也能破坏男性逻辑和象征秩序的一致性。
按照齐泽克的说法,经典的蛇蝎美人是对父权统治的支持:她代表了父权符号宇宙的“内在侵犯”;她一方面“是男性受虐狂-偏执狂幻想中的性饥渴与施性剥削的女性,同时她又支配我们,享受她的痛苦,挑衅我们去暴力地占有她和虐待她。[41]”因此,蛇蝎美人的“威胁”是虚假的:作为对父权统治的支持,她代表了幻想客体的外化,使得不可能之实在成为了一个障碍。蛇蝎美女是“一种必要的,但不能被公开设想的幻想的形式,所以它只能出现在明确的叙事台词中……她受到惩罚,然后男性主导的秩序被重新确立。[42]”这就是经典的蛇蝎美人。不过,后现代版的蛇蝎美人和这个有很大不同
在新黑色电影中,如劳伦斯·卡斯丹的《体热》(1981),约翰·达尔的《最后的诱惑》(1994),保罗·范霍文的《本能》(1992)中,是蛇蝎美人获得了胜利。她通过“残酷地意识到男性的幻想,并在'现实生活'中执行幻想”,最终颠覆了男性的幻想。后现代蛇蝎美人通过“给他们想要的东西[43]”最大程度上颠覆了男性的统治。在林奇的《妖夜慌踪》(1997)中,我们能发现两个版本的(经典的和后现代的) 蛇蝎美人。齐泽克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两种“女人”之间的对立的一种元评论。
齐泽克对《蓝丝绒》和《妖夜慌踪》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因为前者是从田园诗般的小镇生活沦落到黑暗创伤的底层社会,而《妖夜慌踪》则是在黑暗的底层社会和“正常”日常生活的绝望和疏离之间摇摆。换句话说,对后者而言,日常生活当然不是田园诗般的;相反,它是大他者秩序的压抑和异化。 因此,《妖夜慌踪》呈现的并不是正面现实和负面现实之间的对立;相反,它呈现的是两种恐怖之间的对立。
在电影中,我们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幻想消解的场景:一种是有关世俗日常生活的彻彻底底的枯燥乏味;另一种代表了对第一种幻想的幻想性支持(幻想光谱),而在齐泽克看来,后者非但不是前者的崇高版本,反而是其残酷、淫秽和残忍的一面。因此,按照齐泽克的说法,电影提供了在糟糕和更遭之间的选择,两者之间的转变都准确地发生在(男性)主角性行为失败的时刻。
第一次发生在弗雷德和蕾妮之间,当时弗雷德不能让他的妻子高潮(因为他的阳痿),然后被妻子施舍似地拍了拍后背。弗雷德在电影中经历了一场精神病式的转变(一种潜在的幻觉)。在他发现蕾妮被谋杀,自己被定罪后,弗雷德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也就是皮特。在这个角色的伪装下,皮特开始机智地与暴徒埃迪先生/迪克·洛朗和他的情妇爱丽丝——蕾妮“转世”的金发女子进行接触。当爱丽丝告诉皮特“你永远得不到我!”时,性关系不存在被再次明确,皮特又变回了弗雷德。
齐泽克把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帕特丽夏——蕾妮和爱丽丝——解读为崇高客体即对象小a的两个不同面。在从“正常”的日常夫妻转变成新黑色宇宙(neo-noir universe)的过程中,对象a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第一部分中,作为障碍的对象小a是内在的——如同拉康的名言 “性关系不存在”;而在第二部分中,作为障碍的对象小a被外化为禁止性行为积极的障碍:即埃迪先生。
障碍的最终结果便是主体没有得到(不可能的)享乐之物(das Ding),或者康德的物自体。大写之物就是原始的“失去”——即主体性的空洞,后者由幻想对象的实体对象小a填充(这就是为什么拉康幻象公式是:$a;“被划杠的主体”——即主体性的空洞——与幻想客体的相遇。)因此,主体只有在无法触及物的情况下才能参与象征现实。因此实在界是以某种空洞或裂缝的方式置身于象征界中。另一方面,主人能指在象征界之中遮盖了空洞,对象a则从象征界的背面填补了这个空洞。这个空洞藏匿于表面之下——匿于幻象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将对象a称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崇高客体”让我们得以在“后意识形态时代”中的后现代语境之下,解释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它代表了病理性的补充——一种“前信仰的信仰”,甚至超出了“虚假意识”或质朴意识的范围。齐泽克接受了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观点,利用“崇高客体”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在意识形态末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会是犬儒主义。对于齐泽克来说,马诺尼(Octave Manoni)为了解释“恋物癖式的否认”而发展出的精神分析公式能够非常好地解释犬儒主义: “我很清楚,但是……”(Je suis bien, mais quand même...)。正如斯劳特戴克所说,犬儒主义是“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是“出现在质朴意识形态与启蒙之后的意识状态[45]”。对齐泽克来说,犬儒主义是(正如他在《捍卫失落的事业(In defence of lost causes)》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在”大解释”已经不够的时代诞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当旨在解放的大型政治工程不再引起共鸣时;当“常识”告诉我们“最远也就是开明的保守自由主义……没有可行的资本主义替代品……(只)剩下其本身时,资本主义的波动便会破坏自己的根基。这不仅涉及经济的波动…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治的波动。在这一层面上讲,问题的答案既不是哈耶克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不是粗糙的保守主义,更不应坚持老旧的福利国家理想,而是应当将经济自由主义和最低限度的社群“威权”精神结合……从而抵消该体系的过度(excesses)[46]”时。只有这时,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出现。
齐泽克对“后理论”的反动性和保护性立场,及其对大理论的“反革命”攻击,表示反对与拒绝。而前文所讲的,正是其表达反对意见时的语境。“后理论学者”的态度或多或少地代表了盛行当下的犬儒理性——那就是断定“大理论”之终结的态度
参考文献:
27. It is difficult not to assume here that iek is relying on Fredric Jameson’s
MarXIan notion of modern allegory developed i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28. iek, “In His Bold Gaze,” 219.
29. This is how iek views the Stalinist Communist who perceives himself as the
object- instrument of History; the Stalinist Communist is a sadistic pervert
who sees himself as the means of carrying out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iek,
“ ‘In His Bold Gaze,’ ” 220.
30. Ibid., 223.
31. Ibid., 226.
32. Ibid., 229.
33. See Joan Copjec, “The Orthopsychic Subject: Film Theory and the Reception
of Lacan,” in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34. See Todd McGowan, The Real Gaze: Film Theory after Lacan (Albany: SUNY,
2007).
35. iek,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 Verso,
1994), 114.
36. Ibid.
37. Ibid., 115.
38. Ibid., 117.
39. Ibid., 120– 21.
40. Ibid., 121.
41. Slavoj iek, 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 On David Lynch’s Lost Highwa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10.
42. Ibid.
43. Ibid.
44. See Slavoj i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18.
45.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trans. Michael Eldred (Minneapo-
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 5.
46. Slavoj i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 2008), 2.
关注电影帝国公众号,订阅更多奇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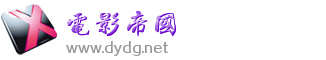 电影帝国
电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