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棉郎_弹棉花_NEW YORK_小剪刀
一年一度的清明百家饭在喧闹中开始,又在喧闹中结束。饭桌上的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是我所不愿的。于是早早地丢下筷子,下了桌,径自回到了房间里。门外的热闹依旧,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这泛黄的信。
不免地,我回想起来今天早晨随大队去扫公墓的情形。同一房的叔伯们大都扛着锄头,手拿镰刀,脚上套着雨靴。唯有我常年求学在外,疏于使用这些“亲切的老伙计们”,只能两手空空,跟在后面,还需要提防脚下的坑洼陷阱。与叔伯们相互沟通的最大困难是,你无法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和辈分。每每从外地返乡,若偶尔见了面,则需尴尬而不失礼貌地问候一句:“您出去摘菜了呀?”,这个时候往往得到的回到是:“是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然后就是简单的寒暄,再走向各自的陌路。但是那些人一直在你的记忆里,从你小时候第一次参与扫墓,一直到现在。岁月无非是在他们的脸上多刻画了几道印痕,鬓角多催生了几缕白丝。自从记事以来,他们不就是那样满脸皱纹吗?
但是今年有一丝异样。我总觉得队伍里少了谁。我们到了一处公墓。照例是要听叔伯们讲述这些墓的来历。有些墓是没有后人的。这些墓主人,生前勤勤恳恳,为后代积福积德,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偶然间便绝了后。于是每年清明,只能禄受我们这些旁支后代烧去的纸钱了。
我嚼着刚刚采摘的茶耳朵,回味着甘甜中带着的一点苦涩,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那些久远的故事。忽然间,我的余光瞥到了那一块特别的墓碑。即使是绝后墓,都会在碑石上写明墓主人的生卒年和子嗣、配偶情况。唯独这一座墓的碑石上空无一字。忽然间我终于明白了今年是谁少了。
我怯怯地问了一句:“那个每年都会来扫这座无字墓的大伯,怎么今年不见过来呢?”
“死了啊,就今年正月刚过就死的”。某位大伯云淡风轻地随口回了一句。是啊,有谁在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离去呢?故乡于我而言,在那年背着书包,扛着行李去往北方的时候,就只有冬夏,再无春秋。白发的离去与黑发的降临,不过是我在和邻里小心翼翼地聊天才能得到的消息。这位大伯的离去,只不过是意味着有一个面孔再无出现的可能了,对吧?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他的名字。从很小的时候,我们这些野孩子都在背地里叫他“弹棉花的”。我们村的曾曾祖辈,都是亲兄弟,他们把土砖房呈两排并列建造,中间是弄堂。又由于两排房子挨得很近,顶上的瓦片完全遮住了中间的弄堂,里面常年没有阳光。孩子们都称那个地方是鬼怪出入的地方,是捉迷藏的禁区。于是等到我父辈的时候,大家早已搬出去,都住进了自建房。弹棉花的却一直住在那排房子的最里面。
有一回,我被“汉奸大队”追击。好几个小“汉奸”手中挥舞着竹竿,末端缠绕着白色废弃薄膜。那薄膜划破空气,发出嘶嘶声,同时耳边传来“抓住那个土八路”“八嘎呀路”“你地,死啦死啦地”等口号。这千军万马的骚动,下一刻就要把我这个“八路”吞没,然后拉到村东头的槐树底下,趁着最毒的日头,进行“打靶练习”。我是知道那练习的:被抓住的人需要笔直站立,两腿紧紧并拢,双手则用不知道哪里捡来的蓝黑色尼龙绳象征性地捆住,然后引颌上扬,不屑于看那些汉奸们,在雨点般的“枪声”袭来之前,喊上一句“我日你妈!我们革命主义者是杀不尽的!”,然后顺势倒向老槐树。我向来是不爱说脏话的,可每次的英勇就义环节却必须完整,总让我感到难为情。我心中惧怕又要“被英勇就义”,于是加快了脚下的逃跑步伐。
人们总是在情急之下做出事后无法理解的决定。就比如说,那一天在躲避追捕的时候,我的双腿似乎被魔鬼施了法术,不由自主地迈向了那漆黑的弄堂。当他们看见我的身影闪进了“禁区”之后,一个个都不敢再向前迈出一步,仿佛脚底下的乌黑泥土里埋藏着狡猾的地雷,随时都会跳出来一口咬住他们的大腿,然后轰然爆炸。
“好你个小子!说好不可以去那里面的!你赖皮!”
“就赖皮,就赖皮!有本事进来抓我啊!”我疯狂地往弄堂里面跑去。可没跑几步便有些后悔。头上的瓦片遮天蔽日,里面一片漆黑。我摸着墙壁,蹒跚着往里走。黑暗在旁边只笼罩了一小会儿,我的双眼就适应了这微弱的光线。于是,我便看到了他。
我以为弹棉花的是坐在地上,仔细一看,原来是坐在他家的门槛上。这木质的门槛不知道是哪一辈的祖父亲手安装上去的,被无数人踢踏而过,如今中间已经呈现凹槽,正好可以供人随意坐下。他左手握着银色的水烟袋,正低头吸着烟嘴。烟袋里面传来咕噜咕噜的水声,这让我想起来在唐小冬家看的一部黑白动画:一只白熊在河边咕噜咕噜地大口喝水,喝完水后猛地用两只后脚站起来,然后张口血盆大口……。随着他的吸气,烟丝发出明亮的红色,然后又迅速地暗淡下来。弹棉花的转过头来,缓缓地向空中吐出白雾。
透过烟雾,我看到他头上罩着脏污的毛巾,在微弱的光线下,干瘪的脸上挂着下坠的双颊,几颗老年斑点缀其中。他张嘴问了一声“小夏?”。我看到他仅剩五颗牙的口腔一张一合,显现出深不可测的黑色喉咙,里面似乎有一只黄色的小手要伸出来,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瘦小的我生生吞下。我哇的一声,还没等眼泪落到地上,就闪出了弄堂口。
于是,在我们的孩童群体中,那个弄堂里存在妖怪这一个传言,就进一步给坐实了。
但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已近残尾之际,父亲竟然把妖怪请到了家里来。那是一个仍有暑热的傍晚,我刚从学校返回家里。弹棉花的正坐在我家饭桌旁,双手托着水烟袋吞云吐雾。桌上是一只红花大瓷碗,里面装着黑色的液体—这应该是母亲常年会熬制的各种消暑去热的汤药。我心中升起一股嫌弃之意:等他喝完了,就去把碗给打碎。反正现在家里不正缺一片刮丝瓜的瓷刀吗?
“小夏,你放学回来了啊?”他说这话的时候,努力用下垂的脸颊挤出一个微笑。
我没有理他,而是径自走向自己的卧室。很快,饭桌上的红花瓷碗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父亲从阁楼上面背下来一块长方形大木板。母亲用湿抹布小心翼翼地把木板擦了个遍,然后把我冬日里常盖的棉被剥了外套,倒出来一块硬硬的、表面呈黄色的棉内芯。弹棉花的旋即上手,用一把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黑色小剪刀利索地减去固定住棉芯的红色棉绳。哎!陪我度过无数个冬日寒夜的棉被,就这么惨死在弹棉花的手上!
接下来的场景就像是施展酷刑一样,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直至今日。只见弹棉花的搬出一块黑色的铲头,上面长满了三五厘米见长的钉子。他一把抓起棉被,卷成一个大捆,用一只瘦小的铜褐色臂膀掖住,然后抵在那块铲头上。他只轻轻一个下滑,我亲爱的被子就白肉横飞了。如果,它体内也曾奔流过血液,那么此刻一定是血溅当场,一片狼藉。该死的弹棉花的!连尸首也不放过!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棉被已经破碎成无数块了。父亲和母亲在一旁帮忙把一块一块的棉絮聚拢,一齐堆放在擦洗干净的木板上。弹棉花的脱去上衣,露出上半身,然后转身去取靠在墙边上的棉弓。他背上呈半C字形的棉弓,把两块由木头弯曲而成的腰带环在腹部,然后猛地抽紧布带。我看到他没有任何肉的小腹瞬间被收紧,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只怕他瘦弱的身躯下一秒就要被生生勒断。他左手扶着棉弓,右手拿着棉锤。这棉锤头部是圆柱体,上面的黑色纹理和黄色包浆渐次交错。供人拿手的那一端是圆锥体,最顶部绑了好几圈灰色布条。我能想象得到,那布条原先应该属于某一条洗得发白的废弃裤子。弹棉花的用棉锤击打牛筋制作而成的弓弦,弓弦快速往复震动,发出低沉的声音,像一把松了弦跑了调的古琴。他把弓弦靠近棉花块,棉花沾到弓弦后被带起到空中。但还没等棉絮逃走,下一锤已经到来。于是棉絮在这不短不长的距离上,随着弓弦恣意翻飞。原来,弹棉花的其实是一个音乐家,一位为棉絮伴奏的音乐家。
那年冬天,我拥有了一床“崭新”的棉被。我在内心里除去了他妖怪的形象,走出来一个背着棉弓的干瘦老头。但是这个干瘦的老头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又变成了一个古怪的疯子。第二年清明,父亲第一次带我跟随大队去扫公墓。所有人都不言不语,脸上是肃穆的表情,二三十人的队伍,都统一穿着青灰色的衣服,像一条从冬眠中意外苏醒的巨蟒,在清明早晨的迷雾中穿行。这条巨蟒时而因为河流拉得很长,时而在上山的时候紧缩成一团,它长着镰刀和锄头的脚,所经过之处,树木和杂草都被它踩倒,在后方留下一条新开辟的大道。终于它爬上了我们此行的公墓所在地,身体瞬间解体,各自四散开来。我跟随在父亲后面,他正在用手拔去一块碑石后面的绿色嫩厥。“这个地方公墓少说得有100多座,”他站起身来,转过头望向山脚,“你看山脚下,我们刚上来的那块平坦的地方叫飞机坪,再往前面是王家坝……”父亲在后来的每次扫墓都会这么说,许是怕我忘了来时的路。
一声哀嚎,打破了出发以来的肃静。我朝声音那边望去,弹棉花的正坐在一座墓碑前悲哭。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只见他双腿盘坐在地上,清明的雨水浸湿了他的长裤,他双手抓着红色的泥土,痛苦的眼泪如豆般滴落。那块碑石上竟空无一字。父亲还在那边用洋火小心地点着三根朱香,其他叔伯也完全没有被这边发生的事情吸引,兀自做着手上的活计。
父亲说,那块无字碑只不过是个衣冠冢,当年在修建山脚下的飞机坪的时候,有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过。因为也没有见过尸首,无法确定他们的生死,于是那座无字碑,就是对他们共同的纪念了。弹棉花的,每年清明都会去那里痛哭一番。那么,他应该是在为他消失的亲人哭泣吧?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中午随大队扫完墓才得以解答。当时我正在屋内玩着游戏,随着一声爆炸声,我方的水晶轰然倒塌。Defeat。我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眼神迷离地看着窗外。村委会的杨主任,他拿着皮夹子,正在和我的母亲交谈着什么,母亲在把他往屋内引。“小夏,杨主任有事情找你!”母亲在屋外呼唤着我。
“小夏,听说你回来了?”
“嗯……学校放三天假”
“这样啊,杨叔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听说你在大学当老师了,是吧?”杨主任讪讪地笑着,一边接过我母亲递来的热茶,然后坐在了竹椅上。
“是啊,杨主任。我今年刚去的,教英语”,我客气地接过话茬。
“那就好,那就好……小夏,你还记得老幺吧?”杨主任忽然这么问。我一头雾水。我在回忆里仔细地搜索这个名字,但是任凭我如何回忆,也记不起来这是哪号人物。
杨主任见状,才笑笑说:“哦,你们这些小辈应该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们应该叫他……嗯,弹棉花的,对吧?”。我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
“是这样的,老幺不是今年年初就没了嘛。他无儿无女,更没老伴。他是这十里八乡最后一位弹棉郎了。国家这几年不是在搞非物质文化传承么?弹棉花就是候选项。所以,我们在他去世前,征求了他的意见,让他把弹棉花的一整套工具都捐给了政府。他走了以后,我们在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这些东西,你给看看,是什么东西。”说着,他从皮夹子里面掏出来一个信封,递给我。
信封是那种黄色牛皮袋的材质,很旧,但是却没有一丝的折痕。右上角盖着一个褪了色的邮戳,原先应该是红色,上面隐约可以看到“New York”字样。我轻轻地打开信封,里面是几张泛黄的信纸,展开来看,是一封英文信。我这才明白杨主任的来意。我仔细地阅读着,里面的内容令我震惊不已,于是,我开口问那个以前从来不愿意问的问题:“杨主任,老幺以前的故事,你知道吗?”。
“他的故事,我是知道一些的,我相信你大伯知道,你爸也知道,村里的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应该听说过。其实不用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就能猜出是谁的来信。今天来,是来找你证实一下”
“那能给我先讲一讲他以前的故事吗?”我现在有点后悔,为何小的时候不缠着长辈们给讲一讲呢?杨主任点点头,开始了他的讲述。
老幺在没有变老之前,也叫老幺,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为了糊口,他就去跟着老师傅学习没人学的弹棉花。每年夏秋交割的时候,他就背着棉弓,跟在师傅后面,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帮弹棉花。那年他大约十四五岁,以前只在外面世界回来的人口中才存在的遥远战争,一下子就逼近到了眼前。那天他师傅正在给一家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姚姓人家弹棉花。这家人因为离老幺那边的村落远,两三年才招老幺他们进去弹一次棉花。老幺一边用磨盘压着棉絮,一边听他师傅和姚家主事的聊闲篇。
“哎哟喂……这个世道真的变了啊。”老姚挑起了话题
“嗨!变就变呗!谁当皇上,咱们老百姓的日子不是照过的嘛!”师傅答腔。
“我说你个老弹棉花的!一天到晚就知道弹棉花!这日本人打过来了,仔细你第一个被抓走!”老姚半开玩笑地说道:“我跟你说,我前天进山的时候,看到一伙穿着灰色衣服,背着步枪的人!他们就躲在那个树林子里头。他们见到我,就喊我老乡,让我回去挑了一担米给他们,我吓得不轻,哪敢违抗。于是就给了他们一担米,他们倒是也和善,给了我三块大洋!三块啊!”
“哦豁!三块啊!小心啊,他们是好是坏都不明白呢!别被钱蒙了眼睛”师傅反呛了他一句。这个时候姚家的女儿回来了,老幺第一次见到了她。我们并不知道老幺和这位姚小妹是如何好上的。我们只知道这一次见面后,他们经常一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下。他们离成婚只差一次上门提亲。但逢此乱世,家徒四壁,身无分文,老幺哪有勇气上门提亲呢?
有一天,老幺正在家中煮野菜,锅中不时翻起墨绿色的汁液,老幺闻着这气味差一点一口吐了出来。这时他师傅在门外喊道:“老幺,来活了,新妇棉被!快背上棉弓,随我走!”。老幺在后面跟着,随口问了一句“哪家嫁女儿啊?” 他师傅没有答话,只是在前面走着,半晌他吐出了几个字“老姚家,一个大洋工钱!”。这几个字像晴天霹雳,把老幺震得五荤八素。他像一具灵魂出了壳的尸体,无意识地翻山涉水,到达了姚小妹家。迎接他们的还是老姚,他见到老幺也一并来了,脸上显出一丝愧意。他准备解释一番,叫道:“老幺,我知道这样很不好。但是你得为小妹考虑一下啊……”
“师傅,今天我来主弹吧!”老幺脸色铁青,手上暴起了青筋,随后又消退下去。他师傅也无话,在后头替他套上腰带,勒紧布带,他瘦弱的身体与棉弓相对比,显现出不和谐的滑稽感。老姚抱出来一床旧棉被,帮着拆解,撕碎。老幺右手拿起前几日为自己打制的趁手棉锤,放在弓弦上,弓弦低吟,像风吹过山谷;他重重地锤了三下,弓弦有些急促,带起了棉絮,他师傅想说什么,但还是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接着老幺开始急促地敲击弓弦,手中的不再是棉锤,是一把长剑,这把长剑刺破了棉被,棉絮在空中飞舞,像是狂风骤雨,落个不停。“够了!老幺,你一边去!”师傅终于喊了出来。这滂沱的大雨,戛然而止,空气中还有雨珠在缓缓下落,在接触到脚下泥土的时候,瞬间被吸收,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似不曾下过雨,好似他不曾出现。
老幺被逐出弹棉房。他站在屋檐下,看着潺潺流下的溪水,听着屋内传来的歌谣声,那是师傅在按照惯例,唱起弹新妇棉被必须唱的曲:
弹棉花咯 弹棉花咯
半斤棉弹成了八两八哟
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
弹成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
哎哟勒哟勒 哎哟勒哟勒
弹成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
那个姑娘要出嫁
“老幺哥!”有一个声音从角落里传来。老幺发现姚小妹就在墙角处,探出来一个脑袋,在轻声呼唤他。老幺往房间里眺望,确定没人注意到他,他向姚小妹靠过去。“老幺哥!你可算是来了!我本来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不过,现在不怕了,我有办法了”小妹的脸上显出一丝兴奋。
“怎么?”
“我不要嫁那个又老又丑的王富贵!但是我爸逼着我嫁!我想好了,我要进山去帮忙修飞机场。山上当兵的跟我说,现在早提倡婚姻自由了,他们愿意替我做主。他们最近在一个美国佬的帮助下,在秘密修建一个机场,作为补给站。那个美国佬吃不惯糙汉子们做的饭,我正好可以去帮忙做饭!等机场修好了,好几个月就过去了,看我爸能拿我怎样!”姚小妹真的很机灵,老幺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他就这么觉得,如今这个计划应该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他只得点头同意。果然,姚小妹偷偷去帮修建机场。因为此事涉及军事机密,姚家人也无法让她立即回来,于是只得退了婚事,等待机场修建完毕。
一晃过去了几个月。一天晚上,老幺从睡梦中惊醒,他听到轰鸣声从上空划过,床板都被震得吱吱作响。几分钟后,又听到十几声爆炸。他赶忙跑出去,看到飞机场那边火光冲天。老幺被远处迅速传来的地层震动一晃,一个跟头栽倒,昏睡了过去。
等到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四散的残肢已经收拾干净,他跑过去的时候,只看到好多个大坑布满了飞机坪。那些穿灰色军服的人紧急撤离了,没了踪影。老幺后来的一生,再也没见过穿灰军服的人,以及姚小妹。他只得每年去那衣冠冢前凭吊。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姚小妹在那场空袭中幸存下来了,因为,我手中的这一封英文信件就是出自她之手。
Dear Lao Yao,
I never expected to have this chance to write a letter to you. I heard that the situation in mainland China had changed so I presumed that this letter would be sent to you successfully. I survived that air raid. Now I am in New York, but I think I owe you an explainantion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then.
What happened on that night still appears in my dreams occasionally. The air raid claimed more than 30 of the soilders. I was boomed into faint and when I woke up on the next morning, I found myself lying on a stretcher heading to the make-shift military hospital. Mr Smith, the American engineer who was helping building the airport was also transported to that hospital. One of his legs was completely blowed up. I stayed there to attend to the injured on account of the lack of nurses. I tried to send messages to you but failed as I could tell form your non-response. Inevitably, I found myself obsessed with Mr Smith while I was nursing him. Therefore, our wedding was witnessed by the paients in the hospital three months after the raid.
Later Mr Smith, my husband, received the order from his superiority to return to Shaghai. I followed him. The war ended soon and Smith took me to the USA. Unfortunately, as you know, I did not know how to write in Chinese before I left China. So my husband taught me to write in English. That’s why I am writing to you in Englsh. I hope you can find someone who can do the translation for you.
I have given birth to three sons and one daughter. I have had a happy life here. How are you going now? I really hope you have also got married and had a happy life. I wish we can see each other in the future when the situation gets better.
Yours,
Xiao Mei
1985.04.22
我为杨主任讲了信的大致内容。杨主任怔怔地坐在竹椅上,半天没有回应。母亲又端过来一杯热茶,杨主任才回过神来,道了一声谢谢。临走的时候,他回过头来问了一句,:“小夏,你觉得老幺是否找人给他翻译过呢?” 杨主任许是知道我无法给出答案,问完之后,并没有听我回话,就扭头离去了。我想,这一封1985年从异国他乡的来信,老幺无需要看懂内容,便可猜到是谁寄过来的。至于他之后仍然每年都去墓前凭吊一番,是为何而哭呢?
在我回学校的前一天,我去了老幺的墓前,除了给他烧去纸钱,还给他做了迟来的翻译。纸钱在烟雾中腾空而起,透过烟雾,我又看到了在烟丝微弱的红光照耀下的老幺,他正惬意地抽着水烟。
关注电影帝国公众号,订阅更多奇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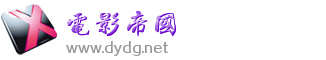 电影帝国
电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