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周】面具_痴男怨女_英雄冢_功劳簿
一年前,天窗。
森森的牢房里,滚着潮湿的冷意,角落里不知什么啃噬着腐烂的肉,发出琐碎又令人胆寒的声音。
这个名为天窗死牢的地方,地处一片郊区野林中,是一个深入地下的牢房。这里一扇窗也无,全靠牢房的管道送气,里面不辨百日黑夜,易于使犯人失去对外界的感知。
牢房外,周子舒在送气管的入口处微微皱眉,似是凝视着什么。跟在身后的下属见他迟疑,主动蹲下身去翻找,并未找到半点不妥。周子舒蹲下,摸了摸草地里的晚露,抬手看着指尖的水渍,若有所思。
“今天犯人招了么?”他沉声问道。
下属立刻应答:“不曾。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一遍。就差七窍……”
周子舒扬手打断他,站起身说:“知道了。"
还未入秋,天气凉了三分,入夜后便成了七分的冷。周子舒脚蹬棉靴,虚搭着一条有点重量的黑色棉袍,步履坚实的走到地牢门前,盯着门上的铜环反复查看。跟在身后的下属,不知首领何意,也不敢擅自去推门。
周子舒花了些功夫,确认此门无人进入,才不着痕迹的将它推开。
向下的阶梯涌上一股地底下的味道,混着翻上来的泥土腥气,不大好闻。周子舒的七经八脉里正流窜着蚀心的痛,从头到脚没一处舒服的地方,被这味道一熏更是难受。
可他脚步未停,一步一阶的走了下去,直至最里面的牢房。
一个妙龄女子被锁在牢房的椅子上。她被破破烂烂的衣服裹着,满脸污泥,浑身是血,皮肉翻飞,如葱的十根手指均被拔秃了指甲。
显然她已经受了不少刑罚,此时恐怕是进气儿多出气儿少了。
跟着周子舒的下属面露不忍,轻轻地咳了一声来纾解心中的异样。周子舒却面无表情地围着她转了一圈,仿佛眼前的一切存在的理所应当。在天窗首领眼里,红颜白骨,并无分别。
他在女子面前站定,冷冷的开口:“她在醉生梦死里,看见了什么?”
牢房里的守卫知道是问自己,便上前行礼作答:“她看见了自己被心爱之人所杀,死得其所。”
周子舒微微皱眉:“痴男怨女?无聊至极。可有什么有用的消息?她是不是晋王的人?”
守卫面露难色,顿了顿方说:“试了十几种法子,犯人约是不认识晋王的。不过,也不能全然确认……”
大家都知周子舒的严苛,没得到的情报,谁也不敢乱编。
想知道一个人是否认识另外一个人,并不算难。毕竟,人与人之间一旦相交,就会在万千思绪里种下一颗种子,无论怎么回避,总能在反复的讯问中探得一点枝丫。
“约是不认识的”,便是个保守的答案。
周子舒一年之内,已经钉入四颗要命的钉子。此刻对于他来说,朝廷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都不再是他所生之年在意的。只要这个人不是晋王来窥探他的,是其他什么人,并不要紧。
“给她打七窍三秋钉吗?”下属小心翼翼地试探。
周子舒缓缓的摇头,命令道:“不用,直接杀了。”
守卫和下属均神色一凛,齐声说:“遵命。”
周子舒刚一转身,变故就发生了。他身后的女子猛的睁眼,眼角流出血泪,继而耳口鼻中均是血流不止,犹如地狱野鬼降临人间。
离得最近的守卫被女子喷了一脸污血,好不亥人。周子舒的听力已经弱了,见了守卫的样子才回头看她,只见她如回光返照露出渗人的笑意,参伴着口中涌血的“喝喝”声,用尽力气地漏出字句:“谢……谷主……成……全……”
在她声嘶力竭的疯狂言语中,刚刚还站得笔直的守卫和下属,纷纷栽倒在地,七窍冒出暗红的液体。
周子舒暗道一声不好,压住口中的甜腥血气,运起“流云九宫步”功奔出牢房。通向地面的阶梯上,横七竖八地倒着天窗的人,周子舒已顾不得他们,强提出一口气出得地牢的门,眼见四周无人来袭,又继续发足狂奔。
是毒。
若不是因为深夜是七窍三秋钉发作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这么晚才发觉。
————
周子舒踉踉跄跄的离开林子,不敢回到自己住处,而是寻了隶属天窗的一间秘密空屋,脱了外衫,暗自运功,腾气调息。
钉子的苦痛与不知名的毒药叠加,使得周子舒并未发现身后跟着个尾巴。
他一路狂奔,有一个红衣男子便一直跟着他。
那人脸上戴着半阕银色铁面具,用面具遮住眉眼,只露出挺鼻薄唇。大红的衣衫上只着了一条极窄的腰带,腰间别着一把素扇。他的脚下是不露痕迹的绝顶轻功,衣袂翻飞,好似月下一只轻盈火苗,在深夜街巷的屋檐瓦楞上跳跃,最后停在周子舒运功疗伤的房顶上,轻轻掀开一个瓦片,优雅地做起梁上君子。
这人正是鬼谷谷主,温客行。
鬼谷有鬼私自离开,本不至于劳动他老人家的大驾。可那个女鬼偏偏在逃离后,一直向谷内传书信,说是甘愿为了他才破戒,为他找寻儿时伙伴。他向来厌烦这种自作多情的人,又恐怕消息传递中漏了信,便亲自追出谷来,今日还亲手处决了她。
温客行感到厌烦无聊。是如何不开眼的女子,非要触他逆鳞。在他的计划完成前,他可并不想寻找什么儿时玩伴。鬼有鬼要做的事,贪恋人间旧情,是要遭报应的。
鬼主用的是“红尘失魂”,这是一种鬼谷秘制的毒药。此毒无色无形,只是一缕腥甜气味,被人吸入后,一炷香的时间才会发作,中毒者七窍流血而死。
温客行早在地牢的通风入口处放了毒丸,待更深露重,露水将丸药划开,毒气便飘入地牢,把里面的人全部毒死。令温客行意外的是,有人能从这毒药里逃出生天,不仅能连逃十几里,还能自行运功逼毒,可见其功力深不可测。
午时三刻,是温客行最喜欢的时辰。
星照荧灰,月笼流银,万家灯火俱灭,不用看人世熙攘,偏能偷得半刻清风。
温客行对此人深感兴趣,便不急杀人。
他依在房檐上,透过一个瓦片大的孔洞观察那运功祛毒的人。因他寻的角度稍偏,只能见其背影,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屋子里只点了一盏油灯在桌上,忽闪忽灭地映着床上的男子。男子散了发髻,黑头入瀑地散在床上,他只着白色里衣,却因运功而不停冒汗而湿透,修长的脖颈带着点点水渍,弯成一个极美的弧度。
温客行情不自禁,喃喃叹道:“这对蝴蝶骨,平生仅见。灯下美人醉,诚不欺我。”
他说话声音极低,却还是惊动了正在运功的周子舒。周子舒背脊一紧,立刻向上抬头,大声喝道:“是谁!”
周子舒刚一抬头,温客行就身姿凌厉地从屋顶破瓦而下,瞬间摘下自己的面具压向周子舒。他故意把面具原有的开孔错位遮在周子舒的脸上,遮住他的眼鼻,只露出周子舒的唇来。
周子舒正在运功的紧要关头,不敢妄动出手,猛地被一下子剥夺视觉后,更是强迫自己沉着应对,张口道:“有何贵干?”
三招两式之剑,温客行已将错位的面具绑紧于周子舒脑后,他微微退身,从上到下打量起眼前的人,发觉此人前身的骨相,也是完美至极。锁骨深陷,腰细腿长,即便遮上脸,也是位大大的美人。
不自觉地,温客行言语间多了几分狎昵,笑说:“放心放心,我只劫色,不掠财。”
周子舒听他要劫色,而不是要他性命,反而定下心神:“可是不巧中了毒,身体僵硬气味难闻,不如阁下换个人吧。”
温客行见他说话十分对脾气,低声赞道:“功夫高,还会讲道理,妙哉妙哉。既然你觉得中了毒不方便,我先给你解毒就是。”
周子舒登时变了脸色:“原来这毒,是阁下的手笔。”
温客行悄声走近,俯身下来,鼻尖从周子舒的脖颈一路嗅到腰处,又巡回他的耳边吐气如兰地说:“哪里气味难闻了,明明香汗扑鼻。”
周子舒做了十数年天窗首领,指着他破口大骂、背地里暗自诅咒他的人多如牛毛,他本以为自己早能无视任何人的言语,不想碰见这样的孟浪之词,立刻大怒:“离老子远点!”
温客行对他的发怒十分满意,笑意更深:“这么烈?”
周子舒深吸一口气,才缓缓道:“我见你与那女人不像是一伙,倒像是她的仇敌。正好,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万事好商量。”
温客行却道:“我可不稀罕什么朋友。美人儿,解毒之前,先给我香一个,怎么样?”
身为天窗首领,周子舒深谙刑讯的技巧,现在落入人手,只能一边暗暗运功,一边与他拖延,将话头转开:“江湖上惯用毒的,除了蜀地唐门,就是西南沐府。听阁下口音,似是北地生人,并非出自这两家。”
温客行的手已经附上周子舒的发额,听了这话便手下一顿,取出扇子抖了抖,堪堪依在床栏边上与他对话:“不错。美人学识渊博,还对我如此有兴趣,不妨继续猜猜?”
周子舒挑唇一笑,继续说道:“阁下为杀一人不惜灭了一个地牢的守卫,手段狠辣,又不惜做梁上君子采花大盗,莫说不是名门正派,连小门小派也不会如此五毒俱全。可你身法凌厉,轻功还在我之上……你,你做什么?”
话音戛然而止,周子舒突然顿住,是因温客行在他说话之间,已俯下身来,用拇指按上了他的唇,细细摩挲。
“笑得美,忍不住。”温客行道。
温客行的拇指压着周子舒的唇角,来来回回地勾勒的下唇形状,忽轻忽重,挑逗不已,仿佛要把他唇上的纹路拓印在自己的手指上一般。
“怎么不接着猜我身份了?”温客行问道,也并不希望对方真的答他,见那人微微发抖,便得寸进尺的捏住周子舒的下巴,一口亲下去。
周子舒气得在对方摸上来的时候就有准备,两人的脸刚隔着银色的铁面具撞上的瞬间,周子舒便用尽力气去咬温客行,温客行眸色一暗,用扇子将人拢入怀中,与他对咬起来。
先是一场野兽的般撕咬,不得章法,以牙齿为利器野蛮行事。然而温客行是风月场的高手,手上花样也多,这撕咬到后面也渐渐变了滋味,缠绵旖旎起来。温客行见怀里的身体越发瘫软,知道对方得了趣味,便放肆大胆地在对方的口中用舌模仿交媾的样子,进进出出,好不风流。就在他伸手去掀对方的衣服时,对方突然牙关狠闭。
要不是退的够快,温客行恐怕是第一个“被咬舌自尽”的人。他用衣角擦了擦自己嘴唇,只见大红的衣角上都是暗红的血迹。
假意温柔,看准时机反攻,倒是用心伐谋之人。温客行啧了一声,点头言道:“真烈。”
还未待他进一步动作,周子舒那边已然解了毒性,他在温客行怀中猛然推出一掌,用了十成十的功力。
温客行放开手臂,不疾不徐,起身后倾,转扇相挡,继而连退数步,真心实意的赞了一句:“好俊的功夫。”
周子舒懒得与他废话,亦起身下床,向他拍去第二掌,电光火石之见,两手交手了七八招。周子舒深觉自己吃了没有兵刃的亏。无奈他的软剑和暗器都是藏在外衣上,他只着里衣,一时摸不到兵器。情急之下,想到脸上的面具不比扇子弱,便抬手去摘面具。
原本温客行与他见招拆招,想探他武功门派,可见他去摘面具,立刻变了脸色,丢下一句“哎呦美人,后会有期”便起身运功,蹬墙而上钻出屋顶的洞,很有些落荒而逃之意。
待周子舒摘了面具,眼前哪里还有登徒子的身影?
他刚刚逼出毒气,不宜再追,只好就此罢了。摸着床栏上剩余的温度,周子舒啐出一口血,用手摸着嘴唇,回味道:“哪儿来的疯子。”
然而今生今世,周子舒再也尝不到这样的滋味了。下个月,第五颗钉子打进来,触感就会丧失得更厉害。
如此想着的周子舒,把手指上沾的不知是谁的血擦在面具上,小心翼翼地将面具收了起来。
————————
面具之事的一年后。
温客行杀了白无常后,心情依然无丝毫好转。
他对人伦纲常、仁义道德毫无兴趣,众鬼出谷时他也没想如何约束他们,可一旦有人扰乱他的计划,他变难以忍受,杀之都无法解恨。
无论是为了一己私欲,还是打着“帮他”的旗号行事的,他一概是杀了了事。
望着白无常挂在梁上的尸身,温客行莫名想到一年前,自己用“红尘失魂”之毒杀死的自作多情的女人,还嫌她死得过于舒服体面。
他又想到那个晚上遇见的内功高手。萍水相逢,热烈一吻,丢开便两厢忘却,当真潇洒自在。那高手的身形比阿絮的宽广些,阿絮比他多了几分病态。
或许正是这几分病态里的豁达样子,才让他如此放不下。
然而如今已经多想无益,左右是阿絮已经厌弃了他,就算再怎么邪恶疯癫,那个人也看不见、说不着了。
是夜,温客行走入阿絮曾经住过的房间,那里已经没有了心上人的身影。
温客行躺在他睡过的床上,难以入眠。他的脑海里一会儿是杀父杀母之仇,一会儿是众鬼惧怕他的样子,一会儿又想起他为阿絮吸取肩头毒液时候的嘴唇触感,紧跟着“你是真疯”的一锤定音,一颗心忽冷忽热、仿佛裹着冰块在烈火里烧一般难受,不由得愤恨地锤穿了床板。
没想到床底下锤出个暗格的边角来。
温客行蓦然起身,一边念叨“阿絮不亏是天窗出身”,一边以指为刀干净利落地拆开床板,不一会儿就拆出个枕头大的暗格,里面放着个暗色梨花木的小箱子。
他不由得想,“是他的么?他负气而走,不带它,是还要回来的么?”
温客行暗暗想着,以蛮力撬开箱子上的锁,上面是好几张人皮面具和易容所用的工具,还有一些银票银两。温客知道这是阿絮的私物,行心中大喜,于是一件一件细细拿出来把玩,翻到最后,竟然是一张银色铁面具,上面还有斑斑血迹。
端一看那物,温客行就觉三分眼熟。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研究一阵后,温客行瞪大双眼,果真在面具内里的角落处发现了自己的标记:一个小小的扇子形状的暗刻刻纹。
“是他!”那晚的灯下美人、寥寥几语和互相撕咬的回忆扑面而来,惊到了温客行。在他把“那个人”和“阿絮”渐渐重叠在一起之后,连他自己也没发觉,他激动得手都抖了起来。
我那样对过阿絮。
阿絮知不知道那晚的人是我?
阿絮留着面具是喜欢我那样对他?
温客行的脸上渐渐露出笑意,而后越笑越深,最后愉悦地笑出声音。鬼主近日来心中的阴霾全部化为乌有。他回到客栈里自己的房间,哼着小调换了一套衣服,准备去把他的烈女哄回来。
————————
周子舒靠在城墙根喝酒,嘴上念叨着一些有的没的,心里却只有一句话:原想寻个埋骨之地,偏还重遇那疯子,当真死都死不痛快。
不过,被掳的张成岭从他头上飞过,打断了他的所有纠结心肠。
那小子可是他见阎王时唯一可说的善行佐证,要是没了,他和阎王说什么去?
周子舒进到张成岭被绑架的房间,从蝎子手里护住便宜徒弟,自己的七窍三秋钉立刻按时发作,经脉流转不周,吐出一口血来。
他想,今日就算是拼了性命不要,也不能把这黄泉路上唯一的功劳簿给弄丢。恰在此时,温客行怒发冲冠地冲进房间,深情又惊又俱,比阎王煞气还重。周子舒先是一喜,知道今夜这功劳簿已经稳稳的保住,继而又心念直转,陷入了一丝困顿与迷惘:这下子他娘的死不成,要如何面对那疯子呢?
他只见温客行的身法招式,前所未见。他招招狠辣,全是照着敌人最痛的对方下手,显然打定主意让蝎子生不如死。周子舒从前就很不耐烦这样的打法,现下他就快看不见也听不见,若是在蝎子面前倒下去,丢的是祖宗的脸面。
“老温……”周子舒开口叫了一声,温客行立刻会意,杀招尽出。
周子舒一晃三摇,被温客行从张成岭的怀里接过,整颗心定下来,安心放下戒备,昏昏睡去。
————————
不知过了多久,周子舒从客栈醒来,不过却不是自己的天字号房间,而是温客行的房间。
房中无人,窗棂里透进了光。只是窗外是朝阳还是夕阳,他已经无从分辨。以往白日里,要命的钉子肯放过他一些,今天他却听不到外面的虫鸣鸟叫。
他躺在被褥里,眼前的床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周子舒知道,是昨天夜里与蝎子动武,消耗太过,一时三刻缓不上来。——也说不定时辰已到,再也缓不过来了。
房门被人推开,周子舒的脸上感受到了一阵微风,下意识的笑了笑,暗道触觉还在。
来人一袭青色衣衫,手里端个盘子,周子舒便知道是温客行了。他勉力坐了起来,温客行将吃食放在桌上,自己坐到他身后为他运功,三刻钟后,周子舒自觉耳目灵敏不少。
温客行坐到周子舒身前,轻声问他:“喝点粥吗?”
周子舒撇了一眼桌上,摇了摇头:“不用。把我的酒壶拿来罢。”
温客行知道二人心结未解,也不恼他冷淡,只是点头说好,去门口吩咐了小二送酒进来。
周子舒想趁机从床上站起身,却发现他只是抬了个胳膊就从指间痛到肋骨之下。他强压下满身的不适,好歹把双脚挪到了地上,坐在床边对着桌,方显得不那么虚弱。
两人各怀鬼胎,就着桌子喝了一壶酒。
温客行一直觑着周子舒的脸色,一面心疼他夜里受伤吐血,一面又对着沾了酒气、水润晶莹的唇想入非非,不敢直视太过,眼神躲躲闪闪。
周子舒只当他终于对那场吵过的架生出了愧疚,以为他是乖顺知错,又羞于开后,只好先张口打破了沉默:“成岭呢?他怎么样?”
温客行以为吵架的事情已经揭过,立刻喜上眉梢,道:“在隔壁。那小子死活要拜师学艺,我先帮你应承下来了。”
周子舒挑眉道:“你凭什么帮我应承?”
温客行见他并不反对,知道自己作对了事,只道:“他是个好孩子,又一心想要习武,与你又投缘。你从前孑然一身,现下有了……咳,有了徒弟,也是一桩喜事。我便罢了,你这样讲究的人,有人为你送终,总是好的。”
周子舒听他说“我便罢了”的时候,不高兴的眯了眼睛。但想到二人之前争吵,又强压下来,喝了口酒掩盖下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子舒心想,他是将死之人不打紧,但若四季山庄的武功没落,却是对不起恩施,便点头说:“这样安排也好。”
温客行一抖扇子,摇了个翩翩自得:“我是阿絮的知己,所以想你所想。”
周子舒最看不得他这副嘴脸,冷哼一声,却掩不住嘴角的笑。阳光透过窗,晒着他的背,也照着眼前温客行微微发光的俊朗面孔。温客行与他相对而坐,因是坐在桌前的矮凳上,比他低半个头,此刻正在用那双好看的桃花眼,深情许许的望着他。
不知怎么,周子舒有了一丝晒到阳光,全身盛暖的错觉。
“你这个人啊。”周子舒如叹如诉,“实则比成岭那孩子,更需要人护着。”
温客行一手执扇,另一手捏着袖子里的银色面具,正在踟蹰如何拿出来与他的阿絮相认,猛地听到周子舒这样说,满脑子的龌龊全跑了个精光。他九岁入鬼谷,在魑魅魍魉中心如闪电、杀伐果决,从未有人对他说过“要人护着”。这句话放在心尖上念上几遍,只觉得一身的冷血,都要化作万古柔情,心里那阵又冷又热的感觉,比深夜难眠的时刻,更加磨人。
周子舒见他脸色古怪,勉力向前探身,问道:“你怎么了?”
温客行再也按捺不住,将大半个身子探过桌子,捏住周子舒的下巴便吻。他本想要像那日一般,狠狠撕咬占有,可是触上那片柔软的唇时又不自觉的卸下力道,改做轻咬啃噬,温柔厮磨。
和上一次一样,周子舒知道他要做什么。
周子舒本是可以躲的,但被亲上来的瞬间,他却微微翘起了唇角,好似他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所有前尘往事,四颗钉,七颗钉,责任与恩怨,在他渐渐离开的时候替换成,一个吻,许多吻,自由与知己。
两人皆带着酒气,唇舌相交,温客行只觉得他的阿絮醇香醉人。周子舒悄悄地向后倒了倒身体,以手肘向后撑住身体,离开了温客行。温客行先是不解其意,而后见到心上人笑意盈盈,便喃喃一声“阿絮”,便扑到床边,把周子舒揽在怀里。
温客行有些不敢置信,自己在白天的清醒时分,人间尘世里,获得了他心上人的真心。这是他妄想得到,不配得到,却偏偏得到了的世间珍宝。
周子舒全身都疼,稍微转了转身,找到一个舒坦的姿势,用背靠在温客行的怀里说道:“温柔乡,英雄冢。我虽不是英雄,得个温柔乡做冢,也很值得。”
四下皆静,两人各存心思的回忆了刚刚的浅吻。仿佛谁动一动,就打破了彼此的梦境。
良久,周子舒抬手勾了一把温客行的下巴,语气豪放地说:“想什么呢?小爷的酒还没喝完。”
温客行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笑,拿起桌上的酒杯,含了一口酒,低头便渡给周子舒。沉浸温柔乡的周子舒,只得吃力地攀上他的脖颈,以指尖勾住温客行后颈上的肉,张嘴努力承接。
周子舒对身体的控制力正在减弱,嘴角有些不受控制地漏出酒水,从唇角到下颚划出暧昧的水痕。原本很辣的酒,在他口中与水无异,可温客行灵巧的舌让他品出了不同的滋味,他心中一动,轻轻含着它,试探着,用齿尖咬出一点血来。
习武之人,对血的味道最敏感。只是一点点,周子舒便觉得,他又闻得到,尝得到了。
温客行已是激动得眼角绯红,想到面具相隔的那一晚如何激烈,更是肆无忌惮的吻怀里的心上人,恨不得把平生所学全部施展出来,引他的阿絮动情,与他共赴巫山。可渐渐,温客行发觉了异样,他怀里的人越来越冷,越来越沉,最后竟然有昏迷之态。
温客行只道他是内伤过重,体力不支,只得恋恋不舍的把人放回床上。周子舒迷迷糊糊,摸着他的胳膊,找到他的衣角说:“我之前,藏了一张你的面具,现下在你的衣袖里,刚刚我摸到了,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偷人私物。”
听到这个,温客行只能将那铁面具拿了出来,轻声在他耳边说:“阿絮,这原本就是我的东西,何来偷窃一说?”
周子舒却抚上他的脸说道:“老温,你依然有很多面具戴在脸上吧?也无妨,你藏好罢。”他的手指顺着温客行的脖颈滑到胸口,“我知道,这里藏着的是什么。只有我知道。”
温客行把这只手捉在手心里,与他十指交握道:“你睡会儿吧。”
周子舒还想说,你我相见,红尘失魂,有些东西就分不清是你的还是我的了。——然而他已经口不能言,只得把这段话藏下。
他的容颜,他的声音,他的气味,他的唇舌,他的肌肤,周子舒都一一记下,放心睡去。
五味皆可念,天真不回头。
关注电影帝国公众号,订阅更多奇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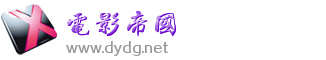 电影帝国
电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