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界、崇高之物与齐泽克电影理论:第一章 从电影理论到后-理论(上)_电影理论_齐泽克_电影理论家
象征界、崇高之物与齐泽克电影理论
原名:The Symbolic, The Sublime, and Slavoj iek’s Theory of Film
原作者:Matthew Flisfeder
翻译:祖国人、柴来人
校对:傲傲傲娇的风学长
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资本主义法权,请联系并提醒原po卷铺盖删文跑路。

齐泽克和拉康派电影理论
很多当代拉康派电影理论家认为在拉康精神分析学派重拾对电影理论的兴趣这件事中齐泽克是功不可没的。齐泽克对拉康精神分析的哲学重读影响了许多电影理论家,使他们重新审视早期拉康电影理论家所发展的一些问题,这些理论学家大多在1960年到1970年间构建了关于电影和观众的精神分析理论。他们中包括了尚-路易鲍德利,克里斯蒂安·麦茨,劳拉·穆尔维,科林· 麦凯布和史蒂芬·希斯这样的名人(仅举几个例子)[1]。这些拉康电影理论(尤其是观影理论)的早期采用者,采用的是拉康前期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建构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他的作品crits和前期的研讨会中。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建立在三个层次的探究之上: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他的许多早期作品专注于前两者,而将实在界置于背景之下。然而,正如许多当代拉康派学者指出的那样(尤其是齐泽克和琼·柯普伊克),从拉康的研讨会七:《精神分析伦理学》(1959 - 1960)开始,拉康的研究轨迹开始从想象界和象征界转移到实在界,以及另一些颇具争议的概念:“物”(das Ding),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小a),以及后来在他最后的研讨会上提出的“死亡驱力”、移情、幻想、享乐(jouissance)、同情[2]。尽管拉康的思想变化与许多电影理论家开始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建立理解电影观影和电影意识形态的概念模型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然而在早期使拉康的思想与电影理论适应的尝试中他的后期思想是缺席的。比起像对象小a(对象-欲望的原因),幻想,享乐或者实在界这样的概念,拉康的早期采纳者选择了他先前的理论概念,强调想象界和象征界的重要性:“镜像理论”“缝合”和“凝视”。
拉康的理论被大量使用也使得他的理论招致一系列的批评。批评首先来自1980年代研究精神分析概念的女权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玛丽·安·多恩、康斯坦斯·彭利、杰奎琳·罗斯和凯莎·西尔弗曼的作品3。例如,罗斯是最先指出拉康早期理论不足之处的拉康理论家之一,特别是关于麦茨和让-路易斯·科莫利作品中提及到的拉康的“镜像阶段”和想象界。同样罗斯也认为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缺乏对“性别差异”的关注[4]。她和朱丽叶·米歇尔在《女性性别》(Feminine Sexuality)选集的引言中给出了对拉康的性别差异理论更详细的解释。该选集也包括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拉康后期著作的最早的英语翻译版[5]。然而,这本书仅试图澄清拉康理论的细节,而不是拉康精神分析在电影理论中的应用。齐泽克和琼·柯普伊克对拉康电影理论的哲学介入对后者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柯普伊克的著作《阅读我的欲望:拉康反对历史主义》(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1994)以探讨拉康理论误读的一章开始,根据她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电影理论中经常把拉康的“凝视”理论和福柯在《惩罚与规训》中提出的“凝视”概念混淆[6]。正如现在的学者所熟知的那样,早期的拉康电影理论主要集中在拉康的“镜像阶段”概念上,以解释观众/主体与电影中的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关系[7]。然而,柯普伊克指出,早期电影理论“对拉康理论的‘福柯化运用’与早期对拉康的误读使得他变成一个‘“挥霍无度(spendthrift)”的’福柯”[8]。柯普伊克所指的把拉康理论中的“凝视”福柯化的表现在麦茨与穆尔维的作品中特别明显。他们仅仅引用了拉康在“镜像阶段”中对“凝视”的定义而忽略了在《第十一次研讨会: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3 - 1964)中,拉康对“凝视”的实际理论化,拉康在此强调的是“凝视”是客体的,而非主体的。凝视是对象小a的视觉驱力(scopic drive)。托德麦高恩最近在他的书《真正的凝视:拉康之后电影理论》(The Real Gaze: Film Theory after Lacan ,2007) 中提出了这一反思。
与他和希拉昆克尔共同编辑的《拉康与当代电影选集》(2004)一样,在《真正的凝视》中,他也赞赏柯普伊克和齐泽克使“生命(life)”这一概念回归到拉康的电影理论中去。尤其是齐泽克,他已经对当代拉康的电影阐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麦高恩和昆克尔的选集中发现的拉康式的电影解释,使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也同样体现在最近一期由麦高恩编辑的重点研究齐泽克与电影研究的关系的《国际齐泽克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ek Studies)中[9]。
正如麦高恩在他介绍齐泽克与电影的《国际齐泽克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有很多人反对齐泽克在他作品中实践的对电影的解读(engagement)方式。这种方式有种“消除他所解释的文本的特殊性,以推进他的理论框架的某个方面”的趋向[10]。众所周知,齐泽克在解释拉康的理论时,主要把电影当做一种辅助理解的工具(exegetic tool)。在许多他早期的书,如《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1991),《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1992)和《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1992)都证明了这一事实。正如他自己指出的,他对流行文化和电影的使用纯粹是战略性的:“我首先举出这些例子,是为了避免使用伪拉康学派的话术,也是为了使我的读者和我自己都能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我的理论观点。”[11]。麦高恩指出:“不像那些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不同文本的思想家. . .齐泽克总是在他分析他自己理论前提的文本中去探索”[12].这种对电影的挪用的高潮体现在他与导演索菲·费因斯合作的电影《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中。其中,齐泽克作为“主持人”在电影里,甚至在特殊的电影再现场景中继续分析电影,齐泽克的读者一定会认出这些场景如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和《迷魂记》以及《黑客帝国》和《蓝丝绒》。《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似乎是齐泽克作品的完美延伸,正如因为正如费因斯所言:“齐泽克自己的作品就像电影一样,”而且“在电影中,齐泽克终于找到了充分表达他思想的媒介。”[13]
因此,许多人认为齐泽克对电影研究的意义仅限于他对拉康理论的重新思考,这使得电影学者在最近的时间里重新使用拉康的理论。正如麦高恩和昆克尔在其选集的导言中所指出的,新的拉康电影理论倾向于更具体地关注“文本解释”,而不是对观众和电影接受的“实证研究”[14]。这种文本解释肯定受到齐泽克的无数拉康的电影解释的影响。然而,尽管有这种影响,许多人仍然拒绝认可齐泽克在电影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卫·波德维尔,批评了齐泽克的电影研究方法。
波德维尔是认知主义电影学者之一,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领导了一个项目,以揭穿旧的电影理论范式,特别是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波德维尔与诺埃尔·卡罗尔合编的《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1996)集中探讨了电影研究中认知主义运动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波德维尔和卡罗尔最终试图驱除他们所谓的“宏大理论”[15]的“恶魔”。 他们在《后理论》一书中体现各自的立场,把“宏大理论”作为靶子,提倡更多的“中等水平”的电影学术或理论(复数的theories,与大写的Theory相反)。随后,“后理论”发展为一场从电影理论走向更严格的电影研究的整体运动,如类型研究、民族电影研究、作者研究、观众研究等,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研究中的“宏大理论”项目。当然,这些都是获得电影学问的重要途径;然而,远离理论的方向几乎没有为电影理论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意识形态研究——留下什么空间。当然,这是齐泽克的理论主要关注的地方。
作为拉康派理论学者,齐泽克毫不客气地实践被后-电影理论学家鄙视的做法——以理论“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为目的的电影阐释。齐泽克《真实眼泪的恐惧》一书进一步引起了电影研究中的认知主义和精神分析阵营的分歧。这是一本对拉康电影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书,它通过捍卫电影理论来对抗认知主义。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可以说是齐泽克的电影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阶段。
波德维尔最近在他的书《光中追踪的数字》(2004)的结尾和他的“电影网站”上批评齐泽克对后电影理论论证的拒绝,强调在齐泽克的工作中缺乏“正经的”电影学术,同时重申他对“大写理论”的失望。正如波德维尔所说,齐泽克是一个卓越的“联想主义者”,他对电影的使用纯粹是解释学的,每一部电影都在演绎理论学说的寓言。[16]
传统上,电影学者倾向于首先考虑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对于电影理论和学术的相关性。在齐泽克的案例中,我们开始看到,通过精神分析,电影学术如何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供启发。齐泽克对电影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他对拉康电影学术的贡献。相反,电影学术与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关。
这种立场因此回避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电影研究”?“这是一个研究领域吗?”一门学科?Lee griessen和Haidee Wasson认为,“学科”是由学术的制度化构成的,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授予权威的程序,其所在地是大学。[17](当然,这标志着大学成为争夺政治霸权的一个场所)然而,电影学术的变化表明,它仍然缺乏统一(至少足以让人们对电影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提出质疑)。学科意味着一种方法论,而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统一。至此,或许将电影研究指定为一个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更为合适。因此,电影学术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与许多当代电影学术研究相反,齐泽克所实践的那种电影学术研究并不是以增加对其对象(电影,电影制作,观影)的认识为中心的。齐泽克的电影学问更侧重于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知识。
齐泽克的电影理论建立并扩展了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项目(主要是在所谓的银幕理论中),持续了整个80年代,并再次在当代拉康电影学者的工作中以热情的姿态出现。然而,后者似乎仍然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增加对电影-客体的知识,而不是对意识形态和主观性的知识。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试图混淆统一的电影研究方法的尝试中——尤其是在英国《银幕》杂志上,一个专注于电影-客体的杂志——我们发现了电影理论与后电影理论之间潜在的争论。
“第一次浪潮”拉康派电影理论[18]
重要的是,回顾拉康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第一波浪潮与1968年尤其是在法国的政治起义非常接近。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人们呼吁电影学界来促成一种特殊的政治批评。但是,电影理论家通过他们对电影的政治分析,究竟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电影与媒体学者长期从事媒体文本与接受效果的政治分析。从早期的媒介宣传研究和社会心理学方法到媒介效果的研究,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模型,再到爱德华·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型”,媒体研究似乎大体上遵循了一个政治轨迹。与此同时,学者们也试图理解媒体,特别是电影的乌托邦潜力。这正是瓦尔特本雅明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等学者的目标,后者当然更关注电视。因此,1968年后学术界对电影的政治反应可以在同一种分化(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轨迹中看到。
在文化和社会理论中,1968年之后的几年有时被称为“左翼转向”。有影响力的文本包括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的三部曲:《读<资本论>》(1965)……。后者或许对当时的电影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在法国,1968年后的“左倾”和阿尔都塞关于“症状批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意识形态询唤与主体性理论的影响,使电影学者对电影艺术与观众的关系提出了新的问题。法国期刊《电影手册》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更多地关注政治解读电影。20世纪60年代末《电影手册》 的一篇社论,“电影/意识形态/批评”(作者是Jean- Louis Comolli和Jean Narboni),表明了当时该期刊关注焦点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他们认为电影批评的目的必然是意识形态批评。他们说:“批评的工作就是看看(电影人的)不同之处,慢慢地,耐心地,不要期待任何神奇的转变在口号的浪潮中发生,帮助改变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每一部电影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由产生它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19]其他学者,如爱德华·布斯库姆和斯蒂芬·希斯,赞成“导演一致性[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和历史的影响,而不是个人表达。”[20]的观点。随后,在电影学术领域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这些目标的理论。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也开始了制度化的电影学术研究。结果,电影研究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教育家”和“激进唯物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这两种趋势可以说是当代电影理论和后电影理论分歧的种子,前者倾向于用政治(即激进的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电影学术,而后者则倾向于非政治(看似中立的)教育方法。这两者或许可以更好地看作是电影学术的解释学/解释主义和形式主义方法的分界线。前者是作为“左翼转向”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起源于一种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
结构主义冲击
早期对激进唯物主义或解释学电影理论的一些尝试源于罗兰·巴特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作品。借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方法,结构主义试图理解语言中所表达的符号的整体系统或“结构”。结构主义对特定符号的个别使用不太感兴趣,因为它对符号系统本身的整体结构更感兴趣——因此,结构主义对主体在意义表达中的作用几乎不感兴趣。法国理论家,如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的方法应用于非语言结构,如巴特的广告和时尚中的视觉符号系统,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中的亲属关系和“符号交换”结构。电影理论家也受到索绪尔语言分析的符号学模式的影响,试图提出电影“语言”的理论。
符号学指的是“符号学”。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21]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既可以历时性地研究,跟踪时间的变化,也可以共时地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可以被捕获。不过,他明确表示,他的兴趣在于后者。他声称,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待语言中的符号系统,可以将语言分为语言(整个系统本身)和言语(系统中的符号的特殊的、个体的使用,以便发出有意义的话语)。
符号本身,即语言的各个元素,由两个元素组成:一个是所指的符号所指定的概念,另一个是能指所表达的词/声音-形象。然而,根据索绪尔的说法,语言本身与“现实”没有最终的、确定的关系,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因此,符号是任意的,但它们的意义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差异关系发展起来的。简单地说,A是A,因为它不是B、C或D,依此类推。同步地,一个意符系统看起来如下所示:(signified是所指 signifier是能指)

一个符号系统中的每一个符号的意义都有自己的意义,换言之,是在同一条“象征链”中,通过它与所有其他符号的不同而获得自己的意义。
基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符号学方法,巴特试图发展一种类似的方法来阅读视觉文本,运用他所说的“二阶”符号系统的意义。巴特对符号学的运用与他所说的“神话”有关,或者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修辞话语形式,将语言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神话是指为了建立和建构言语(parole)而对语言的特殊运用,其目的是对特定意义进行编码。在考虑一阶意义和二阶意义之间的差异时,巴特增加了“显义”和“隐义”的区别,前者是符号的字面意义,后者是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衍生出来的联想意义。
在意义的第一级,在显义的层次上,能指与所指合为一个符号。在意义的第二级,原始的(字面的)符号本身成为一个具有内涵的所指的能指,从而产生一个新的意义。

为了解释这两种意义层次之间的区别,巴特引用了一天在理发店看到的《巴黎-比赛》封面上的一个形象:“封面上,一个身穿法国制服的年轻黑人正在敬礼,眼睛抬起,这个描述必须被理解为意义的第一级,即意义的外延层次。他补充说,“不管天真与否,我很清楚它对我意味着什么: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儿子,没有任何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役,对于所谓的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因为这个黑人在为他所谓的压迫者服务时表现出热情。”后者是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增加的内涵意义。它代表了意义的二阶性和意义的自然化。它给视觉文本本身增加了一个意识形态层面。[22]
在这里不难看出,为什么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尤其会吸引电影理论家。结构主义为电影分析家提供了一种思考电影文本意义产生的方法。在对电影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只需要补充蒙太奇中镜头和图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进一步发展电影的符号学,而这正是电影理论家们的出发点。然而,符号学在电影中的应用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正如菲利普·罗森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进一步发展了安德烈·巴赞最尖锐地构思的“古典电影”这一已经存在的概念。巴赞认为,古典电影“是指一系列形式和风格的界限,这些界限是由编辑和摄影实践的某种基本稳定性以及某些一般惯例所界定的。”[23]巴赞认为,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2)造成了古典电影的断裂,导致了电影风格的现实主义化。然而,正如罗森所指出的,虽然巴赞在对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强调了电影风格的道德意义,但是其他电影理论家试图强调电影结构的意识形态方面,并强调电影不一定代表“现实”,但它所描绘的“现实”总是已经从意识形态的立场中构成的。对许多1968年后一代电影学者来说,电影中对现实主义的强调和对“现实”的描绘与“古典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也就是所谓的“主流电影”)制作之间的关系有关。鉴于主流电影在历史上的成功,电影符号学家意识到了在古典电影风格中定位“电影语言”的可能性。
例如,雷蒙德·贝娄和克里斯蒂安·麦茨都试图通过研究古典电影中的重复和“有规律的差异”来发展电影语言体系。他们声称在叙事电影中存在着某些可识别的组织形式,使得观众能够理解电影。因,结构主义电影语言理论认为,电影中存在一个基于结构重复和差异网络的可识别意义系统。然而,鉴于结构主义的方法似乎暗示了一系列意义的规范性特征的存在,一个政治问题随之而来,正如菲利普·罗斯所指出的:它如何可能偏离规范?也就是说,如果现实主义(读作“好莱坞”/主流)电影被贯穿始终的意识形态所浸透(如科莫利和纳博尼的“A”类),那怎么可能打破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呢?[24]
在1968年5月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一种特别政治化的电影方法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一刻,电影理论家们不仅开始关注电影文本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开始关注对立电影的可能性。如果能够理解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构成方式,以及观众对意识形态文本的认同方式,那么或许就有可能颠覆意识形态。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询唤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的呼吁,进一步开启了对电影意识形态功能的探讨。
意识形态和机器\装置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吸引力来自于他将主体性概念纳入到对意识形态的表象层面的探讨中。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既体现在主体身上、也体现在主体所参与的制度-机构(institutions)之中。他将这些制度-机构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在其著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一文中认为,“为了存在,并且为了能够进行生产,一切社会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对其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25]意识形态作为生产条件再生产的一个核心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对着被统治性政治与经济制度-机构剥削的主体发出呼唤、使他们在认同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错误地认知了自己直接的受剥削地位。
阿尔都塞区分了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必需的两类制度-机构: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包括军队等使用直接武力维持统治秩序的制度-机构。而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简称)则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从意识形态上再生产了统治秩序的霸权。这些制度-机构包括教会、教育系统、家庭、法律、政治系统(代议制议会、政党……)、文化和媒体。正是通过ISAs,个体学会了如何通过特定方式来行为与参与,而那些方式则在物质层面上再生产了统治性社会秩序。
对意识形态问题感兴趣的电影理论家们预见到了将电影视为ISA的巨大潜力。例如,让-路易斯·鲍德利推进了阿尔都塞的ISA概念,以阐述电影文本、电影技术设备(摄像机和放映设备)以及观众参与电影的方式之间的关系。鲍德利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认为,电影特有的光学技术(即投影\projection,运动\motion)和更古老的视觉技术(画面透视)的结合,使电影变成了一种“替代性(substitution)的精神机器\装置,并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定义的模式相对应”。他认为,“因此,电影中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机制似乎集中在摄像机与被摄体(the camera and the subject)之间的关系中”。鲍德利认为,电影的最终意识形态效果是依据支配性意识形态在观众身上创造出一种特定的主体-位置[26]。换句话说,观众被电影装置\机器本身所主体化(subjectivized),将其置于一种意识形态式的主体-位置。
鲍德利在这里,是依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在阿尔都塞的ISA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主张,即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他的意思是,意识形态将个体构造为能有效地物质化(materialize)统治秩序的主体。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这个范畴是一个明确的“人文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范畴。阿尔都塞在对英国康米哲学家约翰·刘易斯对他发起的批评的长篇回复中指出,“主体”的范畴——或更确切地说,作为“历史主体”的“人(man)”——起源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法律范畴。[27]因此,对阿尔都塞而言,主体是一个人在意识形态中所假定占据的位置。这种位置\地位归根结底而言是统治性社会形态的一种功能。阿尔都塞认为,在意识形态所塑造(formed)的主体之外、没有主体可言。意识形态,他声称,将个体询唤为主体。
阿尔都塞解释说,“询唤(interpellation)”是一种产生自ISAs的呼唤(hail)、针对的是那些在意识形态中假定占据位置的个体。这使得意识形态理论家不仅可以考虑意识形态表象的结构层面,还可以进一步考虑表象之结构(structures of representation)如何在符号系统中捕捉个体。在电影理论中,这使得我们有可能思考电影文本与其表象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电影文本将个体捕捉为观众-主体的方式。换句话说,电影理论家参考询唤理论,声称电影把观众“定位”为主体。因此,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询唤理论为电影理论家提供了一种思考电影中的元素的方法,而无论是在文本层面还是在观众层面上,这些元素都生产了一种观众与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认同。然而,对于电影理论家而言,仅有结构主义和意识形态理论还不足以回答观众如何认同电影文本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电影学者开始向精神分析寻求电影和观众身份的理论。拉康,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从电影“语言”理论转向电影精神分析理论的明显选择。毕竟,他因构思了关于无意识的结构主义理论而知名,他广为人知地声称无意识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
关注电影帝国公众号,订阅更多奇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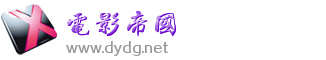 电影帝国
电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