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界、崇高之物与齐泽克电影理论:第一章 从电影理论到后-理论(下)_电影理论_经验性_德维尔
象征界、崇高之物与齐泽克电影理论
原名:The Symbolic, The Sublime, and Slavoj iek’s Theory of Film
原作者:Matthew Flisfeder
翻译:祖国人、柴来人
校对:傲傲傲娇的风学长
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资本主义法权,请联系并提醒原po卷铺盖删文跑路。


进入拉康
拉康派对电影理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1975年出版的一本法国杂志《Communications》所奠基,该杂志以电影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为主题。这并不是精神分析第一次被发展成对电影,乃至文化、意识形态、观众身份的一种理解。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威廉·赖希、弗洛姆都在他们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参考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勾连起来,而许多美国学者也通过(与拉康派不同的)自我心理学发展了各种电影理论。在英语世界,与此相对应\回应的文章评论在70年代末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英国电影杂志《银幕》(《Screen》)上,作者有麦凯波,麦茨, 劳拉·穆尔维和希斯。在其中,麦茨和劳拉·穆尔 维因对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的使用以及在关于电影观众身份的著作中谈及想象界和象征界而广为人知。麦凯波则专注于电影现实主义(cinematic realism),而希斯借鉴了让-皮埃尔·乌达尔(Jean- Pierre Oudart)对拉康“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概念的阐释(由拉康的弟子-米勒所发展)、以此推动了通常被称为“缝合”(suture)的关于电影叙事与观众身份之理论。
拉康派的影响还来自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询唤理论的文章,后者相当多地借鉴了拉康派关于想象界的概念:意识形态描述了一种关于主体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尽管,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指出的,在这个说法里阿尔都塞绕过了象征界、在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识别出了一种关系。阿尔都塞对想象界的关注有助于理解电影理论对想象界这一维度的关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麦茨的论述(麦茨认为电影是“想象性的能指(signifiers)”)以及劳拉·穆维尔“男性凝视”(male gaze)的概念(观众通过此种男性凝视,认同于主流电影中男主人公的想象性“自我”)。
“镜像阶段”与想象界
拉康的论文《镜像阶段作为“我”的功能之构成者》,通常被称为《镜像阶段》论文,可能是拉康著作中在电影理论领域被引用得最多的一部作品。“镜像阶段”理论是拉康在精神分析学领域最早期的贡献,也许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概念。
这一想法最初是在1936年于马里安巴德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第十四届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演讲报告上提出的,后来被修订并发表于1949年在苏黎世精神分析大会上,后者就是文集《crits》收录的版本。
在《镜像阶段》文章中,拉康认为主体自我(ego)的形成大约发生在孩子6~18个月、当其第一次学会识别镜子中所反映\反射的ta的形象之时。根据拉康的观点,孩子会把镜中的图像认同为ta自己的意象(拉丁词imago,小他者意象)。这个意象给予了孩子自以为能主宰\掌握自己的身体的错觉。这个意象就是拉康所指的想象界。
“镜像阶段”所说的“镜子”并不需要是真正的镜子。拉康所谈及的与“镜像阶段”概念相应的“反射性图像”也可能是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儿童通过父母的凝视(gaze)感受到自己被认可的欢欣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儿童认同了ta在想象性的来自母性他者[(M)Other]的凝视中感知到的理想自我。正是通过认知认同与误认之间的对立,自我(ego)形成了,首先是作为一个理想自我(le moi)或者说主体在这一点上将自己认同为想象性的理想自我;然后是自我理想(Ego-ideal,le Je)或者说主体在这一点上想象自己被他者紧盯不放从而想要讨其喜欢。正是在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的运动中,主体从“镜像之我”变成“社会之我”。后者是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钩子。
象征界与能指的逻辑
与当时的许多批判性理论相似,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尤其是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拉康将象征秩序的概念引入了精神分析话语。象征秩序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主体间交流交往在其中发生的结构。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类主体间“现实”的场域。从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交换”概念出发,拉康进一步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33]。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无意识作为某种符号语言向我们说话,而是指身体产生的某种症状性的“发泄”(如神经抽搐)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语言。这些抽搐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主体无意识的信息、而主体自身并不打算以第一人称来表达之。此外,除了将精神分析的概念把握为“谈话疗法”,象征界在处理主体化问题的语言学方面更进一步。
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向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靠拢、以进一步阐明他方兴未艾的具有科学性、哲学性色彩的“回归弗洛伊德”。然而,与索绪尔把所指(signified)放到优先地位不同、拉康赋予能指(signifier)以优先地位。因此,拉康颠倒了索绪尔那里的能指与所指在“横杠”上下之间的位置:

图表1.3:拉康派的所指与能指之关系
拉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展示\证明,任何特定语言的意符链\表意链(signifying chain)是如何通过能指之间的差异而被组织起来的、而不必然需要能指与其所指(概念)的关联。在《无意识中文字的争讼(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一文中,拉康广为人知地通过讨论两扇相同的门的图像而用自己的范式取代了索绪尔。

图表1.4拉康关于两扇门的举例
两扇门(所指,signifieds)是相同的,但我们可以理解它们是如何通过两个能指(signifiers)之间的差异来区分彼此的:“女士”与“男士”。因此,意义不是由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确定的、而是由能指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然而,为了避免“没有事物会具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在拉康的意符链中,我们只被留下了在横杠之上的一系列能指之间的不断转换与横杠之下的所指们——拉康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锚点,或者说是被他称呼为“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的东西,一个将意义逮住的偶然要素。这个缝合点就是所有其他能指通过它们与原初的缝合点的差异而被定义的点。这就是拉康后来所称的“主人-能指”,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它本身就是所要代表的意义。
于是,象征秩序被结构成意指链条、并由固定整个系统之意义的主人能指缝合到一起。因此,一个能指系统中的每一词语都与主人能指的固定功能有关,但与此同时,意义也是在象征秩序之中生成的,因为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人会使用相同的词语来指称特定的对象\概念。例如,我知道“杯子”这个词语指涉什么、正是因为他人用相同的词语来指称这一对象。然而,因为他人在此处不能被简单地缩减为完全经验性的“他人”、象征秩序就指向了拉康所称的“大他者”(grand Autre)。大他者是象征界的秩序。正是在此意义上,拉康认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缝合
拉康派的“缝合”概念是由拉康的女婿、大弟子米勒后来发展出来的。米勒是拉康派的大阀,也因负责编纂编辑拉康研讨会的出版物而知名。米勒认为,“缝合”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思考,能指如何使主体得以进入象征秩序。缝合概念“命名了主体与其话语链条的关系”,定义了这一时刻、在这一时刻主体“以能指的幌子”踏入象征界。米勒的“缝合”概念因此被电影理论家们所采纳、并进一步发展为电影观众理论。在法国理论界中,这首先被让-皮埃尔·乌达尔所提出,他认为缝合概念有助于将电影观众定位于其与电影文本之意识形态的关系之中考察。
乌达尔版本的缝合概念是根据其与正反打镜头的联系而被构想出来的,如卡嘉·西尔弗曼( Kaja Silverman )所说:
电影奇观的观看者将镜头1体验为一种想象性的丰富多彩的画面、不受任何凝视的限制、其中也没有明显差异。因此,镜头1是一个享乐(执爽)的场所,类似于镜像阶段(在儿童发现其与于反射玻璃之中找到的理想形象相异化之前)……然而,观看主体几乎立即就意识到其所观看之物的局限性——意识到一个缺席的场域。在这一点上,镜头1变成了那个缺席之场域的能指,然后享乐也让位给了不快。
观众所体验到的局限性是由对“框架”或者说“屏幕\银幕”的意识所立即唤起的。后者把享乐抛出它自己的领域,并把观者从想象界转换过渡到象征界。在乌达尔的概念里,在屏幕画面的背后有一个观者——也就是说,这将会限制观众感知在画面\画框之外的东西的能力。这个“观者”是“缺席者”(The Absent One ),或者说他者。根据乌达尔,“在电影领域里的所有对象结合在一起、在银幕上形成了它的不在场之能指”。
西尔弗曼解释说,对乌达尔而言,缺席者就是“说话主体”,有些类似于强有力的象征父亲(就像是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里那个部落里的不在场父亲)。作为说话主体的缺席者,会被观影主体即电影观众感知为拥有着后者所缺乏的东西。西尔弗曼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电影观众的缝合理论中,观众会欲望更多的东西。匮乏的观众欲望着看到更多。
电影,在这意义上,为观众带来了不快。西尔弗曼通过引用希区柯克在《惊魂记》中对正反打镜头技术的运用,对这一缝合理论进行了补充。在该片的第一个场景中:
玛丽恩站在她卧室衣柜的门口,她的右侧对着镜头……一张床把她和镜头隔开,在左边的角落里有一张化妆台和一面镜子。突然,镜头向后移动,露出了之前没有曝光过的床上的一个角落,上面放着一个装有赃款的信封。它(镜头)拉近聚焦到了钱上,然后向左摇摄,给了一个打开着的手提箱(里面装满衣物)的特写镜头。在这段时间里,玛丽恩面对着衣柜,看不到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一个镜头切到转身看向床的玛丽恩身上,镜头再一次向后拉、露出那包钱。在下一个镜头里,玛丽恩在化妆台和镜子前调整她的头发和衣服,她转身看向床铺,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关于\来自被盗信封的反打镜头。
西尔弗曼指出,这种手法在整部电影里反复出现,她认为这一场景本身完成了以下几件事:它为玛丽恩和观众都建立了对金钱-客体的着迷。但更重要的是,根据西尔弗曼的说法,这一(镜头)序列将金钱这一物体与一种超验的凝视联系在一起:缺席者的“凝视”。“客观镜头”——对金钱-客体的镜头,而不是玛丽恩的镜头——是具有特权的。根据西尔弗曼,在此我们看到希区柯克试图向观众揭示乌达尔所说的在画面\画框背后“缺席者”的运作原理。这种特征,从缝合理论的角度来看,也许正是使得希区柯克电影比起好莱坞主流电影更具有颠覆性的原因。
乌达尔的电影观众理论认为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是消极别动的,而电影文本自身必须要掩盖这一点。人们可以揣测——如果缝合的运作在真实的经典电影文本或好莱坞\主流电影文本里也发生了——那么拒绝(denying)缝合的运作是否就是使得观众变得主动积极的方式。有没有可能通过禁止反打镜头(counter/reverse shot)来维持观众的享乐、从而足以引起观众身份的断裂,这一断裂进而询唤(interpellate)出一种对文本与(最终是)现实的积极参与?
史蒂芬·希斯同意乌达尔的观点:“作为话语的电影是主体的产物”[39]。在这里也容易看出与阿尔都塞询唤理论的联系——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然而,他补充说,在看不见的缺席者之不在场作为一种结构性丧失(匮乏)之外,还有着其他一些东西的匮乏,特别是主体意欲误认自己、让银幕上的角色来取代(stand in)自己的主体位置。在这一点上,希斯非常接近于劳拉·穆维尔发展出来的“凝视”、或更恰当地说,“男性凝视”概念。
“凝视”
劳拉·穆维尔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文中的明确目标,就是为着政治性目的而恰当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识别出主流电影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但与乌达尔不同的是,乌达尔声称主流电影是通过(by)诱导观众的某种不快感、从而以(through)丧失\匮乏来重新创造欲望的;而劳拉·穆维尔认为主流电源实际上是为观众制造了快感。她声称,这与“父权制\宗法制社会的无意识”相符合,后者“结构化了电影形式”[40]。劳拉·穆维尔认为,父权制社会某种程度上是自相矛盾\悖论的,因为它是围绕着关于被阉割的女性的必要形象而建立的。而正是女性的“匮乏”,“产生了作为象征性存在的菲勒斯”[41]。女性,于是就成为了父权制社会里“他者”的一个能指。
电影是劳拉·穆维尔的兴趣所在,特别是与父权制社会的象征结构有关的电影,因为对她来说,电影是一种“先进的表象系统”、它使人们有可能质疑无意识“结构人们的观看方式与观看中的快感”的方式[42]。然而,她更感兴趣的是看到另一种替代性、另类性(oppositional)电影的发展,这种电影能够摧毁在父权制的观看方式下所生产的各种快感。劳拉·穆维尔认为,主流\好莱坞电影的形式特征反映了它所赖以生产的父权制社会的社会心理强迫症\心理着魔(psychical obsessions)。另类电影的重点应该是对那些反映父权制社会中的强迫症的形式特征做出反抗。这对她来说,需要构思一种新的欲望语言。
主流电影为观众提供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视觉快感形式:窥淫癖(scopophilia)、自恋症(narcissism);前者与将他人作为赏心悦目的对象所产生的的快感有关,而后者则与将自己作为被观看(be looked at)的对象所产生的快感有关。正是在此,穆尔维将她关于电影中视觉快感的观点与拉康的“镜像阶段”联系起来。她认为,“电影有着魅力足够强大的结构,能允许观众暂时丧失自我(ego),并同时强化自我……同时,电影在生产自我理想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在明星体系里表现出来。”[43]她声称,电影形象的力量使主体自身的自我理想(own Ego-ideal)的丧失成为可能,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明星-主人公的形象——更具体地说,是男主人公的形象。
在父权制社会里,观看的快感被划分为主动/男性和被动/女性两种表象。女性的形象,于是,就是为了被看,而男人的形象则是为了在观众之中产生一种认同感。穆尔维认为,电影产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凝视”:观众的凝视、摄像机的凝视、男主人公的凝视。前两种被第三种之能动性捆绑在一块,从而在电影中产生了一种“男性凝视”,而正是后者通过让观众将男主人公的形象认同为对自己的自我理想的误认,塑造了一种观众主体。
在此,作为澄清(男性)凝视的一种方式,希区柯克再次要被讨论一下。《后窗》(1954)、《迷魂记》(1958)、《艳贼》(1964)等电影都将男主人公定位为凝视的承担者、将女性角色定位为凝视的对象。依据穆尔维,让男性和女性角色承担这些位置,表明他(希区柯克)意愿按照一种“意识形态之正当性(correctness)”来进行电影工作。穆尔维指出,就连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也体现了象征秩序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迷魂记》里的警察;《艳贼》里拥有金钱与权力的支配性的男性[44]。《后窗》甚至在杰弗瑞(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凝视着窗外的莉莎时、对电影的观众身份本身进行了调停(mediating on cinematic spectatorship itself )。穆尔维称,这位两人的关系增添了一个情色维度。
想象的能指(Imaginary Signifier)
“缝合”与“凝视”都采用了拉康派精神分析的概念——“镜像阶段”、想象界、能指——以发展一种电影观众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了观众被电影文本所直接询唤的方式。两个概念都表明,电影将观众置于一个由文本本身及其形式特征所预设的特定主体位置。同样,克里斯蒂安·麦茨与鲍德利有些相似,也认为观众的主体位置是根据电影装置(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运作)而产生的。
麦茨说:“电影就像一面镜子”。但电影与镜像阶段的原初镜像不一样,最起码屏幕上投射的图像并不是主体自身的反射性图像。在这个意义上,麦茨不同于穆尔维的论断,穆尔维认为观众在电影中发现的是自己相似之处的反映。之所以(麦茨)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正如麦茨所指出的,主体已经历过了镜像阶段,这使得对屏幕的认同成为可能、尽管屏幕上的形象并不是观众本人的形象。在这一点上,电影已经站在了象征界的一边[45]。但奇怪的是,麦茨声称电影中的能指是一种“想象的能指”。
电影的特点是它的表现对象本身并不在电影院中。在此意义上,麦茨认为电影中的能指是“想象的”。由于电影平衡在场与不在场的方式——它比大多数其他媒介更具感知性(perceptual)——它使我们更多地卷入想象之中。观众自己的形象可能在屏幕上不在场,因此Ta不能将自己认同为一个客体-形象(object-image)。然而,依据麦茨的说法, 观众将自身认同为一个纯粹的、全感知的、先验的主体(pure, all- perceiving, transcendental subjec)。因此,在麦茨的情况下,不是“缺席者”(The Absent One )而是观者自身作为全感知的、先验的主体。但是,与鲍德利的装置理论相似,麦茨也声称观众认同于摄像机的观看。
在电影中存在着一个象征性装置,它为观众对自己的想象性自我认同提供了道路、也使摄像机自身的装置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理解电影,“我必须把被摄对象感知为不在场的(在它的直接现实中),把它的照片感知为在场的,并把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性感为有意义的”[46]后者解释了麦茨如何将电影中的能指识别为想象性的:它本身就是不在场的东西的能指。
依据麦茨,这一点通过电影中的拜物教\恋物癖否认的运作而与意识形态变得更加相关。正如奥克塔夫·曼诺尼(Octave Mannoni)解释的那样,这一点通过下列台词而可得到最好的理解:“我非常清楚……但还是……”(“Je sais bien, mais quand même. . . .” (I know very well, but nevertheless. . . .))观众,当然知道电影所呈现的想象只是幻觉,但还是忽略了这一事实以便被电影的虚构所吸引捕获:“所有一切都被设定为使欺骗奏效并赋予它一种真实的气氛。”[47]
观众的主体位置
不论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电影理论对电影和观众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但似乎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特别是在拉康派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中),即电影是一种生产“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的事业。“缝合”理论认为,电影通过修补客观镜头与主观镜头之间的缝隙(gap)所打开的“创伤(wound)”、来制造消极被动的观众。通过“缝合”过程,缺席者被隐藏起来:电影中的能指的生产,为观众提供了进入电影的象征秩序的入口。观众因不快而被询唤、诱导产生了一种匮乏感和想在电影中看到更多的欲望。相反,“凝视”理论则声称,电影通过给观众提供一个位置、使其可能认同于男主人公的自我理想之电影形象,从而使观众产生快感。电影装置理论——在麦茨和鲍德利阐述的两个版本中都——暗示了观众与电影装置之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认同。在所有情况下,电影理论似乎都表明,观众身份是一种涉及观者直接的主体位置的东西。后者是最近一批电影研究中“后-理论家”们最重要的攻击对象。
在这方面,斯蒂芬·普林斯也许是对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最严厉的批评者。正如他所指出的,电影理论经常忽略关于观众对电影的阐释的经验数据。他认为,“关于人们如何处理、阐释和回应电影形象\图像以及叙事的问题,是经验性问题”,理论建设应该追求对观众的经验性研究、而非教条式地提供关于观众身份的阐释[48]。依据普林斯,(大写的)电影理论中的观众身份之概念,并没有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观众,而仅仅是指“主体”、“理想观众”之类的概念。对普林斯而言,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观众身份概念的最大问题,集中在精神分析所产生的(他认为)不可靠的数据上。这主要与已发表的精神分析案例研究是不完整的这一事实有关——即是指,分析师并不会发表他们在临床实践中的实际记录(notes),精神分析领域也没有既定的\建制的实践标准,因此每个分析师都能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数据。因此,普林斯认为,电影理论家参考精神分析的观众身份理论是没有依据\基础的。普林斯对观众理论的批判意义重大,并提出了后-理论的一些核心关切。
电影研究中的后-理论
大卫·波德维尔和诺埃尔·卡罗尔合著的文集《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1996年)可以说是一份宣言,主张大理论的终结。他们声称,这本书并不意味着理论或理论化的终结。相反,他们声称要结束的是“宏大理论”。他们所指的“大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电影研究中崭露头角的一种抽象思想体系”;“大理论最著名的化身正是从拉康派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变体中派生出来的学说\教条之集合体。”[49]“大理论”指的是波德维尔与卡罗尔称之为电影研究中的“正统”观点,而他们的项目正试图终结之。
依据波德维尔与卡罗尔,后-理论的目标是证明电影研究可以在不借助\参考于大理论的情况下进行,一种中层的研究更适合于发展电影理论。后-理论家们特别感兴趣于证明电影研究可以在没有精神分析理论介入的情况下进行[50]。正如他们所说,这本文集的组织原则是,“扎实的电影学术研究,可以在不使用由电影研究定式所认可的精神分析框架下继续进行。”[51]在这方面,后-理论的核心组织原则似乎不是简单拒绝大理论、而是特别地拒绝精神分析电影理论。
波德维尔和卡罗尔认为,大理论的最佳替代方案是一种“中间层次”或者“中间水平”的研究、这种研究拒绝将电影与“正统”观念引以为豪的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语境(或整体)联系起来。他们声称,后-理论不是建立在“大问题”(或“大解释”)——“宏大理论”之路——的基础上,而是一种“问题驱动(problem- driven)”的研究,这种研究通过对话、测试和经验性研究的方式运作。
后理论中的论文集中在“认知主义(cognitivism)”领域,主要源于对电影观众身份的精神分析概念的拒绝。然而,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声称,认知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其最好被描述为是一种“立场(stance)”。正如他们所称,认知主义分析“寻求通过诉诸心理表征过程、自然过程和(某种意义上的)理性作用的过程来理解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无意识的非理性作用[52]。也许,描述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分歧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了解比较)各自项目中看似是“缝合”的点位:在大理论这边,是以精神分析为其最高参照点的观众身份与主体性理论;在后-理论的情况下,是参照认知理论发展起来的对电影、电影制作者、电影类型、电影叙事等基于对象(object-based)的研究。大理论/后-理论之争,从某种层面上说相当于精神分析与认知主义之间的争论。但我认为,大理论\后理论之分野的说法也是另一场争论的征兆。
大理论与后-理论之争表明了对意识形态(ideology,或称意识形态霸权-普遍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特定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进行理性的、经验性研究之间的分歧。后-理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并不是对大理论的朴素简单反动(reaction)。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关于意识形态与主体性的批判理论的反动。我认为,后-理论是当代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形式。这是对大理论的一种政治反动,而且是在看似没有明显政治化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行动。它试图将电影呈现为一种纯粹客观的东西,这本身是一种精彩绝伦的意识形态性姿态。
认知主义,中层研究,以及对大理论的批判
认知主义的电影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从那时起,它已经发展成为电影和电影研究领域中电影学术研究的主导性途径之一(如果需要加“之一”的话)。与其他电影学术方法相比,“认知主义”的势头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因其对电影大理论的拒绝。尽管认知主义者并不会像某些人(齐泽克)声称的那样、把拉康派单独挑出来PK,但他们确实对电影大理论们很不屑一顾,其中包括拉康派精神分析,其在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中发展而来。然而,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似乎确实在认知主义者的“暗杀名单(hit list)”中占据很高的位置。如果我们考虑到“认知主义”指的是对电影观众身份之精神分析阐释的一种特别拒绝,这就很说得通了。正如卡罗尔所言,认知主义者“把他们的任务当做是回答某些关于电影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电影接受(reception)和理解的问题,而其中大部分问题已经被精神分析电影理论家所提出或至少知晓承认了。”然而,卡罗尔也认为。“认知主义者声称自己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比精神分析电影理论家要做得好得多。”[53]
有人会说,认知主义电影学术研究的发展势头已经成功取代了电影大理论的主导地位。麦高恩甚至认为,今天电影理论“已几乎不复存在”[54]。然而,格雷戈里·柯里等其他人声称,电影理论仍然占据电影学术研究的领导(霸权)地位,他们认为认知主义“经常被忽视或不被搭理、有时被指责为坚持实证主义因而背叛了结构主义之后出现的那些电影研究路径的新颖、激进之见解。”[55]
据称,认知主义往往难以界定\定义,因为它似乎没有提出一套统一的、连贯的学术原理;然而,柯里认为,如果把认知主义视为一种“纲领(program)”而非一种理论、就可以减轻这种困难。对她来说,这个纲领与认知主义思想中的两个中心主题(或可视为“调研规则”)有关。第一个与认知主义者试图在各种不同的表现层次上理解电影的意义有关,如“光与声音的感官刺激、叙事和被赋予更高层次意义与表达方式的对象”。认知主义思想的第二条推论认为,人们用来理解电影的“感性资源(perceptual resources)”,与用来理解现实世界的资源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认知主义者强调一个人对电影图像和叙事的体验与对现实事件的感性理解之间的相似性。[56]当然,精神分析也分享了其中的一些关切;然而,两者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集中在理解与意义之间的差异。
认知主义电影学术研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电影观众身份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挑战者。因此,认知主义者对“正统观点”的其他争论,一方面涉及到对电影学术研究的特别具有政治性(以及,可能也经常是论战性)的方法之关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涉及到其对“宏大理论”的关切。波德维尔认为,电影大理论是“宏大理论”、因其倾向于在这样一种框架中讨论电影:试图解释社会、历史、语言和心灵\头脑的非常广泛而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对他来说,认知主义代表了电影研究中的“中层”研究,它并不试图对电影和观众身份定个大调子,相反,中层研究更加“本土化(localized)”,它关注的是“基于电影(film-based)”的问题,而非更大的社会、政治和心理问题。波德维尔认为,中层研究最突出\重要的领域是“对电影制作者、类型和国别电影的经验性研究”,而传统上被“同性恋、女性主义、边缘群体\少数族裔与后殖民的视角所丰富”。此外,中层研究也帮助电影学者强调了被“正统”电影理论所忽视的其他电影研究领域、如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电影制作者的作品[57]。
柯里认为,尽管认知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持强硬态度,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与精神分析本身相冲突。[58]事实上,一些认知主义者引用精神分析的不同版本来解释电影接受中的非理性模式。[59]认知主义者不如说是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分析理论、这是理解“电影心理学”的关键。大众心理学与感知心理学(Folk psychology and perceptual psychology)是认知主义者最常用的两种心理学方法。因此,确切地说,认知主义者对之争辩的应用于电影领域的精神分析“品牌”,看来是观众身份-意识形态研究中的弗洛伊德-拉康派分支,也就是波德维尔所说的“主体-位置理论”。“主体-位置理论”,依据波德维尔,可以理解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影的社会与心理功能是什么?”波德维尔认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电影理论家们“把电影的概念建立在一些关于社会组织和心理活动的基本假设之上。”
“主体-位置理论”,正如波德维尔所言,将主体\观众视为“既不是单个个人、也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或自我的直接意识。更确切地说,主体\观众是一种认识的范畴、由其与客体和其他主体的关系来定义……主体性(在此意义上)是通过表征系统(representational systems)来建构的。”[60]或者,如斯蒂芬·普林斯所说,电影理论家“几乎没有在经验性程序中的工作传统(也少有看重),他们建构了存在于理论之中的观众;他们几乎没有审视过现实中的观者。”[61]
认知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批评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正如麦高恩所指出的,大多数认知主义者与中层研究者对电影大理论所抱有的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将精神分析的概念应用于电影,而不考虑与该理论不符的经验性证据。”[62]对卡罗尔而言,也有证据表明,一些电影理论家在“理论”与“阐释”之间存在混淆。他认为,有许多电影学者“想象他们在生产电影理论,而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对个别电影进行人为的解读,尽管是用神秘的、‘理论性的’衍生术语”。他补充说,“电影释经经常是通过将理论解读到电影中去来进行,仿佛主体位置的存在——假设是一个因果过程——可以通过阐释学在一部特定电影中找到的在想象界中重述的寓言来证实……当代电影学者不仅假装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技术、一部又一部电影,其证明了一个又一个的普遍模式……电影学者还声称找到了表达出上述理论的电影们。”[63]很难不去设想,卡罗尔在此所谈论的正是指齐泽克。
关注电影帝国公众号,订阅更多奇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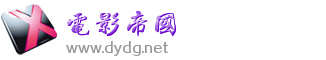 电影帝国
电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