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了一部电影,献给老爸老妈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电影,45岁的导演陆庆屹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因为故事从2013年春天延续到2016年春天,所以有了现在这个片名。电影之外,这家人又有着怎样的生活?请听陆庆屹近日在“一席”演讲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老爸老妈歌词
■演讲 陆庆屹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我爸我妈
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四个春天》,是献给老爸老妈的礼物。
我出生在贵州南部独山县的一个小镇,叫麻尾。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它与一条特别清澈的小溪并行在狭长的山谷里,因此我童年的记忆大多与青山绿水交织在一起。
那里的布依族、苗族村寨比较多,那些民族都喜欢唱山歌,时常在旷野里能听到很远处的歌声。青年男女会在两个小山丘上对歌,选择伴侣。
我的老爸老妈 电影
我妈妈从小酷爱山歌,并且想方设法学唱山歌,几十年下来,她在当地很有名气,红白喜事都有人找她去助阵。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非常繁忙。
我记得小时候过春节,麻尾举行全民狂欢活动。重头戏是舞龙舞狮,还有骑摆马。就是选出七八个小孩扮演戏曲里的古人,骑上马,到村村寨寨去游街,马走起路来屁股甩来甩去,所以叫骑摆马。我3岁多的时候,我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对着小人书琢磨着给我做了一套“摆马英雄”的造型。
我爸爸是个物理老师,性格非常温和,我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发过火。他也酷爱音乐,音乐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几乎每一种他能碰到的乐器,他都会去自学,他一共会20多种乐器。
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乐器,笛子、二胡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除了工作和照顾家庭,我爸爸其他时间都浸泡在音乐里。他曾经说:有你们3个孩子,有那么好的妻子,还有那么多乐器相伴,此生足矣。
我家在麻尾中学的山脚下,可以说开门见山。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生活太困难了,爸妈工作之余,到镇上借来大铁锤,用半年多时间开山,生生辟出了几块平地。又到一里多外的地方,一趟一趟地挑来土,壅出两块菜地,种了各种蔬菜,家里生活才慢慢改善。
但即使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也总是有歌声相伴。除了没有肉吃,我的童年记忆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貌。
老爸老妈浪漫史百度网盘
1998年,我爸妈借钱盖了一个房子,花了半年多时间。但没想到一年后,火灾莫名其妙地发生了。父母辛劳一辈子攒下的一个家,就这样被烧了。
那天我妈不在家,我和我爸面对着焦黑的房间,手足无措,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们在一堆炭黑色的东西里翻了翻,刚买的新电话融化成一团,我姐买的小DV也烧坏了。
我爸从废墟里翻出他的小提琴,背板已经快烧成炭了,他吹了吹灰,叹了口气,下楼去了。我继续在房间里东翻西翻。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到沙沙的琴声,跑出去一看,我爸在天井的井台上拉小提琴。琴声在空旷中回旋,他的动作很轻柔,似乎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听着残破的琴声,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只有音乐可以安抚他。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很久,也觉得心情平复了很多。夜里我们俩点着蜡烛,用柴火煮了点东西吃。
第二天,我妈回家来,看着一片狼藉,浑身发抖。她愣了10秒钟,也没问什么,定了定神就跑到楼上去找照片。我们家的那些老照片,被烧得只剩下大概1/5。
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爸妈说这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
我爸妈年轻时谈恋爱是很秘密的,几乎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妈无意间听到别人嘲笑我爸穷得一双鞋都没有,她跑回家大哭一场,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给我爸。那种鞋一般要做半个月,她3天就做完了。
我的老爸老妈原唱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一口锅都没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状况。但即便是这样,我爸妈每年都会攒一些钱,假期的时候,到县城请照相馆的付叔叔拍一些照片。
我记得有张照片里是我爸给我妈戴花。前两年,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又拍了一张同样的照片,前后相差53年。还有父母在我们家房子前面的留影,这个房子承载了我很多美好的记忆。
这几张老照片都没有被烧掉,命运还算眷顾我们。现在每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翻看老照片,说说笑笑。这些被唤醒的往事,印证了我们的记忆,填补了那些空缺的时光,似乎一个家的光阴更完整了。
北漂生涯
虽然在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但我其实从小很孤独,因为哥姐很早就出去求学了。其他孩子都有兄弟姐妹,而我总是落单的,被排挤也很正常。
我很早就习惯了自娱自乐。上初中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三四点钟起床,往城郊的飞机场那边瞎逛,回来后煮一碗面,吃完背着书包去学校。我会坐在教室的窗台上,看天光渐渐亮起,同学们陆陆续续进了校门,在操场上走过。
老爸老妈简谱
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和人群隔着一点距离,我只是一个观察者。我很少与人交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喜欢写日记,每天都写。当天的天气,遇到了什么事,想了些什么,我都会记录下来。
后来到了北京工作,我很喜欢加班,喜欢坐夜班车。那时候人少,坐在角落里,谁也看不清谁。公交车是不开灯的,只有到站了才亮一下。我就把手伸到书包里,用一只很短的铅笔头在书包里写日记,盲写。写哪个站上来了多少人,灯光是怎么划过的,街上有些什么变化,诸如此类。
1999年,我离开北京,去了贵州罗甸县的一个矿山,因为我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所谓了。但是在矿山,我看到了很多曾经忽略的东西。比如星星,每天都能看到星星。夜幕降临,开始只能看见几颗亮的,眼睛适应黑暗后,星星越现越多,最后布满了整个天空。天空底下,是一重又一重的大山,苍茫茫地望不到边。
我经常坐在山头看着世间万物,感受到人的渺小,也时常为自己的无足轻重而叹息。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具体的影响,但它打破了我的日常经验,促使我观察身外的东西,注意天地的样貌、时间的来去、生命的源泉与尽头。
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2000年过年后的一天,刚刚炸了一个矿洞,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我不知怎么,也不等其他人,点着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声音。
在寂静里,我发现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折射过来,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突然间我被感动了,心想: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蹉跎?
老爸老妈罗曼史百科
过了一个月,我离开了矿山。
回到北京,我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2008年我买了一部相机,拍得很疯狂,每天卡都是满的。
因为拍照,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花花草草、日落月升、街上行人、铺在地面上的光,每一种现象我都很有兴趣。因为拍照需要等待和观察,慢慢地,我不再急躁,越来越安静。
2009年,我注册了豆瓣,没想到这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我在豆瓣上开了一个相册《回家》,就是回老家时,记录父母的生活、田间地野的日常、街坊的往来。没想到这些普通的照片下面,有很多评论,让我特别感动。
这种感动促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去观察那些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离开家20年,我所有的审美、思维、习惯都被重构了,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我回去的时候不需要跟生活较劲了,可以很平和地看待它,很多意义就在这一片琐碎中浮现出来。这些意义可能是诗意的、现实的,也有一些带着浪漫色彩。
《四个春天》
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第9季
最开始,因为对家庭气氛的迷恋,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记录下来的想法,于是我买了一台可以拍视频的相机。
两年多之后,我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他: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侯导说: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很打动我。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为什么不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呢?
我开始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从豆瓣影评里开始搜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建立起我的电影概念。之前我的观影量可能还不到100部,那一年我一共看了800多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十几遍,电影思维慢慢有了模糊的轮廓。
这期间,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有时我会想,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我确信: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人都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对电影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意识到,它比我之前从事过的绘画、摄影更适合表达我的感受。
我想做一部真正的电影来献给父母。带着这种想法,我更细致地去观察父母,从而也更深入地了解到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在他们那个年代,有无数的家庭被淹没了,特别遗憾,我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来献给他们这一代人。
老爸老妈唢呐赵小飞
有了这种驱动力,我就特别有热情,经常背着20多斤重的包和三脚架,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尤其是去山里的时候,为了拍到想要的内容,会跑得更辛苦。
2016年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我出门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问我怎么闷闷不乐,我说我在想未来。他们扑哧就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有!
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其中一个同学腿一软,扶着我的肩膀说:陆庆屹啊,你还是先做我们独山县最好的导演吧。我说:拭目以待。
那天散场后,我回到家里,开始想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的身体逐渐衰弱,我怕来不及了。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剪辑,连剪辑软件都不会用。但是我已经决定开始,带着忐忑的希望。
我光是看素材就花了一个月。然后去找卖我电脑的小哥装了剪辑软件,我请他教我基本操作,他说只会装不会用。但他建议我买书来学,我一下子茅塞顿开,直奔中关村买了两本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把家里的网络全部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工作和朋友。除了扔垃圾和买菜,足不出户,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
老爸老妈浪漫史台词
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和暖气。夏天,我把冰袋泡在水里,用风扇把凉气吹过来,但仍然是浑身大汗。冬天,我穿上两件羽绒服,实在太冷就烧水来泡脚。
最后,花了20个月的时间,剪辑终于完成了。在朋友的奔波下,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愿意安排一场放映,2017年12月30日,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
映前几天,我回贵州去接我爸妈来看电影。我妈大吃一惊,眼睛都快掉下来了,问我: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对呀。她说:是那种大银幕吗?我说:对呀。此前她一直觉得我在胡闹,换了很多很多工作,没有安定下来。
记得有一次她要晾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问: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她问什么是纪录片,我说就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菜去了,我继续跟着拍。她回过头来看我还在,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我笑。电影对小县城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不敢想象。
那天尤伦斯的放映,我像是做了一场梦。映后交流的时候,有观众知道我爸妈也在现场,就鼓掌让他们上台。
我妈很激动,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了舞台,她笑中有泪地对我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成什么样子了!观众大笑。她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对着她笑。
那时我爸已经行动不便了,只能在观众席上站起身,摘下帽子对身后和身前的观众鞠躬致谢。他拿着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颤声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就流泪了。
后来,在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领完奖到后台留影,要穿过一小段黑暗的空间,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很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多零散的往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快速闪过。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发现眼前的场景和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夜晚,在某个领域里,我没有食言,我做到了最好!
解放日报
关注电影帝国公众号,订阅更多奇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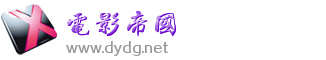 电影帝国
电影帝国